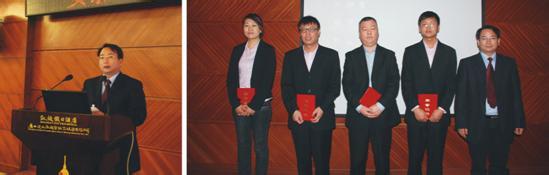长垣南蒲项目十一休整,项目组各奔西东:美女美宁回西安、英伟回北京,刘辉回开封,我因取道开封来南京,因此与刘辉同行。坐在客户送我们的车上,车外是收割过玉米已经深翻过的大片土地,土地酝酿着又一次交媾与丰盛:沉默寡言的土地几个月后又将是一片麦香,没有人知道大地有怎样的感受?
这次南蒲项目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能参与到一场三农改革的实践中去。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正引起广泛关注,通过此书我对三农问题眼界大开,当年也沿着陕西与河南的路线做了一些调查,痛感当年党国将土地一分了之危害甚大(管理无能的表现)。后来也参与过天则、温铁军、胡星斗等专家学者的多次学术研讨,思考如何实现土地集约以获得规模收益,如何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而创造更多社会价值(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后必将到来的是白发时代,中国如果还任由广大农民慢性自杀,那么未来社会负担将会极大)、农村如何有效集中从而便于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有效利用。不过后来我也成为了诗人伊沙大骂的应该被饿死的狗日的“诗人”(不是指写诗的人,而是指矫情忘本的人),我和三农的联系就只有了每年十一回家收割玉米。如果能在长垣南蒲做出一个可以全国或者较大范围内可推广的三农改革典范,功何大焉。不过我知道事情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件事改变的三千年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我对南蒲张书记及其团队寄予大期望。
车在大地上飞奔,就像一只虫子在一棵麦子上爬行。我注意到路边有牌子写着“快速加水,高压冲猪”。一开始我以为书写有误,结果一路不下十块广告牌子皆是如此,我大惑。问师傅和刘辉皆不能知。后来在开封问三轮车大爷才知是在猪的肚子里活生生的加水加气,从而使猪的重量增加,卖个好价钱。 听罢目瞪口呆,为猪为人一悲也!
中午刘辉请我和常师傅在龙亭前的天波一楼灌汤小笼包子馆用餐。饭毕三人散之。我拖着行李沿着龙亭公园外部绕行,有一三轮车老师傅问我是否需要雇车,我婉拒。没想到他就跟在我的拉箱后面不即不离,后来询价,言五元可以送我去火车站且带我沿路浏览御街、清明上河园和开封府。我知路并不近,仔细看了三轮车有动力装置,于是同意了。老人兴致很高,带我去买花生糕点,言称送家里老人佳品。继而就是一路风驰电掣,老人虽华发满头,但是在人流之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让我担心之余好生佩服。开封近些年经济不大景气,下岗工人很多,于是很多人就投入了三产(老人语)。这是一个还在历史和未来中挣扎的城市,给人的感觉灰塌塌的。御街龙亭一带缺乏有效的规划,有点十年前西安大雁塔的味道。可能是职业病吧,感觉景点周边大到楼房色调布局小到垃圾箱颜色样子都不合眼,有点土老帽上身皮尔卡丹下身阿迪达斯的别扭。倒是街边偶尔飘过一个骑电动车的长发美女(穿着现代风情万种)让人眼睛一亮。当然我知道,一个泳装的女子并不意味她精神也同步跨入现代,一个城市民众的生活方式较之高楼大厦更决定这个城市的品味(城市规划是为其穿上超短裙,但是文化建设改造则让这个城市在精神上升华)。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伴随我开封—南京一路。
下榻宾馆,给母亲电话,然后在宾馆里写东西。突然很想听BEYONG的粤语《农民》,那是一种让人灵魂孤独的声音:
如果关上大门孤独过 长命富贵也难快乐

一天又一天 努力耕耘 不停歇
希望在心间
不怕辛酸
永远向前
宾馆窗外是南京的灯火辉煌以及灯火辉煌背后的欲望骚动,我的农民父辈大半在此时(9月29日11点38分)已经沉沉睡去。明天带妻回乡下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