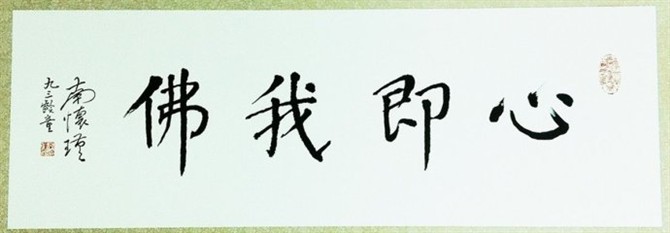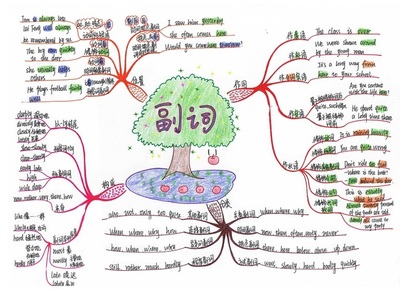“江湖就在民间”,野夫坚信。 从2012年的《乡关何处》,到刚刚出版的《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他一直在以民间修史者的角色,记录他经历的江湖世界,并从中寻找遗失许久的道统,发现简单的善。 问:在体制的力量无孔不入的今天,还有江湖世界存在的空间吗? 野夫:现代社会,已经不允许存在江湖组织,但江湖文化、江湖中人还在,而且还很多。其实,现在很多由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不跟政府合作,自筹资金,有组织地参与扶危助困等活动,这就是江湖文化、江湖精神的一种传承。扶助弱势,为人排忧解难,是江湖精神里最美好、最核心的部分。在过去的江湖里,一个民间组织要有收入,可能去做一些介乎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事情,比如去经营赌博场所,去掌管青楼妓馆,这是江湖的一部分,但不是江湖文化本身的含义。 问:你的江湖世界有一部分是在狱中经历的,你怎么总结自己那四年半的牢狱之灾? 野夫:那四年半相当于读了一个第二学历,我在外边只读到本科,在监狱里读了个“研究生”。监狱生活,“腐烂”是不可否认的,受到很多屈辱也是必然的,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一些犯人身上也发现其美好的一面,就像我写的那个“掌瓢黎爷”,他一怒之下犯了法,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内心深处为人处事的真善美。狱中的四年半,我遇到了许多人,必须承认,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社会渣子、是坏人,但也有一部分是平常人,只是确实犯了罪,他们身上有很多打动我的地方,比如“掌瓢黎爷”。这些人的故事,我烂熟于胸,有一天我一定会写出来。 问:这些人因为你的写作而变得鲜活。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江湖中人”会吸引你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野夫:首先,这些人必须是我认识、了解,进而能够写活的。其次,这些人的故事或者他的人品要足以触动我,使我愿意写出来去感动别人。我记录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可以归为传统的好人,还有一部分,他们不一定能称为好人,比如我写过的那个18岁的杀人犯,不能定义他是个好人,但是也不能定义他是个人渣,他就是一个寻常人,不幸在青春期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他的故事、他的爱情,以及他对嫂子的那种不伦之恋都是真实的。在一个健康社会里,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引发人们深入讨论死刑的存废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孩子,放在今天很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了。其实,经历了他的故事,我自己也常常反思,杀了这样一个人,这个社会就变好了吗?我认为,好的文字就是应该能够唤起人们思考一些问题,这样的思考应该有助于整个国家逐步摆脱野蛮,而越来越走向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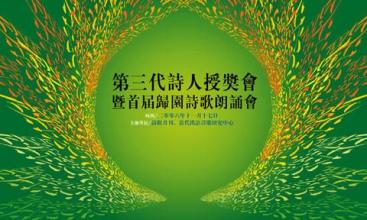
我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不是富裕,是文明。 问:你说过“轻仇的人,必然寡恩”,很多人看你的书,会觉得其中“恨”的情绪太多了,找不到出口,读过之后会觉得心里特别憋闷,感到绝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野夫:我的文章不应该给人带来绝望,但有人读过我的书后,产生了负面多于正面的情绪,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我想这里面有成长背景的原因。现在80、90后的孩子,成长在一个所谓的盛世,没有经历过父辈的贫穷苦难,生命里也极少真正遭遇死亡、歧视和侮辱,也许只在失恋的时候流过泪,当他们打开书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还有这样一些苦难的人群生活过,对年轻人来说,一时间可能不能接受,不敢面对。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写作并不想让人们感到绝望,我希望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希望,看到身边的真善美而勇敢地活着。 问:古语说,礼失求诸野,你的书里记述民间江湖的孝子、义士,是不是一种礼仪精神的传承? 野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支撑国家的四根柱石。在这方面,台湾地区做得非常好,它的国民教育,礼义廉耻是首位的。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已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表明,曾经的礼仪廉耻已几乎荡尽。而没有荡尽的都在民间,江湖就是民间,在这里,我们依旧能够发现无数个光彩照人的瞬间。礼失了,要问道于野,这个道就是道统,就是礼义廉耻。幸运的是,民间江湖正在传承中国的道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