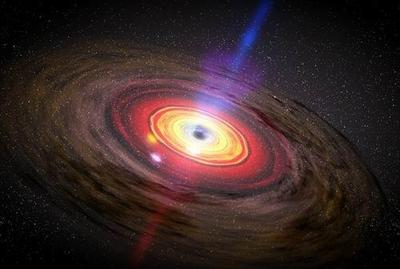□文 高昱
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据说给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个难题,按照之前世卫对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的分级标准,同一类流感病毒的人际间传播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地理区,即需定性为全球性疫情正在蔓延的最高级第六级。自日本出现非输入性病例并迅速在校园传播,世卫组织已经可以提升警告级别了。但日本、英国等国家认为,警告制度不但要反映病毒扩散的地理范围,也应反映病毒的毒性和致死率等。在经历世界卫生大会激烈的争论后,世卫暂时维持了5级的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 这是老规矩遇到的新问题。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日益频繁地利用先进交通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携带病菌的旅行者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比传染病的潜伏期短得多,所以,疫情跨越国界和地理大区变得无比容易,而传统的流行病学标准、隔离方式等显然无法跟上这种高流动性的现实。
现代性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流动性。在一个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四维世界里,前现代社会,空间的演变速度非常缓慢,时间是最活跃的变量;后现代社会则正相反,人们身处的空间环境置换日新月异,由此空间到彼空间的跳跃也倚马可待,时间却仍在以千年不易的速度不紧不慢地流淌,直让人有今日可当千年之叹。然而,无论科技文明如何进步,人们在流疫面前的脆弱似乎总是如一根羸弱的苇草。没错,一场黑死病夺取1/3欧洲人口、一场“亚洲大流感”病死上百万人的往事已难出现,人类不断用知识和技术压缩着传染病的死亡率,但更多新的变异病毒粉墨登场,从猴子、果子狸、鸡禽、牛和猪身上传染给毫无防备能力的人。 危险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降临。全球化让我们消费着日本的猪肉、智利的三文鱼、美国的奶酪,漫长但快捷的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滋生传染病的污染,工业化制造的废水、放射性物质、转基因、生长激素,都可能让生物体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异,而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多,也给病原体提供了更适宜的繁殖条件。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做了太多不知道后果的事,以至于我们搞不清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面对如此复杂的麻烦,现代人的解决之道简单无比:吃药。一个比较陈旧的数据是:我国每年销售解热去痛片和安定片200亿片,对应着平均每人每年服用镇痛药12.5片,一些地区更是高达51片,平均服药年限9.7年,相当于每人累计服用“非那西汀”7.3公斤,对其产生药物依赖者占总人口的10.6%。每年死于对药品过度过久服用的中国人超过20万,因为过度使用抗生素而导致无药有效的逝者不计其数。 一方面文明以扑灭每一路瘟疫为己任,另一方面,它又为每一起潜在的新型瘟疫铺就了温床。到目前为止,在这种竞赛中,文明还是被甩在了后面,而且似乎越落越远。另一个致命的文明难题是,自研制药品在知识产权保护之下变成了一种垄断暴利之后,大药厂们就开始进行挑选性攻关。肥胖、糖尿病、性功能等慢性病、“富贵病”成为研发资源倾斜的主要目标,而多发生在贫困地区的传染病则被选择性遗忘。都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谁愿意耗费巨资为那些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穷人开发药物呢?这次甲型H1N1流感,据说全世界至少需要49亿剂疫苗,但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亲自与30家全球制药巨头代表会面,呼吁制药企业尽快拿出疫苗,并通过捐出疫苗产量的10%以上或者相应降低药价给予穷国援助,但与会企业中做出实际承诺的并不多。只有葛兰素-史克公司承诺在暴发全球疫情的情况下捐出10%、即5000万剂疫苗,还同意向世卫组织在为穷国购买疫苗时提供折扣。另有数家大药厂承诺以低廉价格向世卫提供产量10%以上疫苗,但这些药企的疫苗产量相对有限。其余的“大人物”态度消极。 人们日益把健康和幸福寄托在科技进步和灵丹妙药身上,人的自主性是否会因此而失去的更多、更迅速?商业社会每天都有很多创新、愿景出笼,科技革命总是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满足,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因此更加骑虎难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