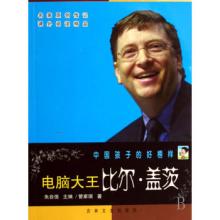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最可能出自中国。2007年4月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时亦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成功将会来自亚洲。英国卡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45岁以下最年轻有为的前10名CEO中,有8名来自中国。2007年年初的《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35年后中国将成全球第一经济体,而美国则仅列第三……。正如比尔。盖茨所指出的:“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哪个国家所决定的。”
真正稀缺的是创新
德鲁克认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社会类型可以从其“首富”的特征中直观地获知。放眼全球,与GOOGLE财富神话相映成辉,印度的钢铁大王、墨西哥的电信巨头及中国的地产大亨,这些新一代的洛克菲勒们正试图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整合传统行业的“炼金术”。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饲料首富”、“钢铁首富”、“房地产首富”、“软件及互联网首富”等完全可能同时涌现。由于后发优势,互联网正是中国少数完全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无疑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
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在资源与市场都日益全球化、流动性泛滥的今天,真正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创新。
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也正是创新,才是我们的最大软肋: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除了缺乏核心技术,我们亦从未出现类似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方式的组织创新。即使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大多拷贝自美国。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WTO前总干事穆尔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当中国的IT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惠于NASDAQ的“中国溢价”因素而获得个人财富的“爆米花效应”时,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尔在总结自己“如何管理30亿美元的公司”时说的话:“大多数公司的发展和成熟的脚步都比我们慢许多,但他们在规模尚小的时候所学到的基本程序,我们这时候必须回头认识。”
对于巨额财富,黄光裕直言“没感觉,假如你在不停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不是财富;如果停下来了,它或许是。但最大的可能是,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不乏“增长速度达到400%”式的狂飙突进,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与GE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还没有哪家中国企业经受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正如任正非在考察了连续十年经济衰退的日本之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北国之春》所说的:“什么叫成功?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与比尔。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记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寓示着脆弱和不确定性。
谁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
曾任美国总统的艾尔文。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公务员热。1999年至2004年6年间全国个体户净“缩水”810万户。除了结构升级因素外,创业环境不尽理想应是主因。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加拿大只需2天,中国内地需111天;再来看注册资本(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内地为1000万元人民币,日本约为82万元人民币,美国则为零。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
对于创业环境,一线的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柳传志曾以“孵小鸡”为比喻形象地诠释“市场温度”的变化。史玉柱曾对媒体叹苦:“我随便写了民营企业的15个死法,随便一条就能把你搞死……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 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面临的更可能是“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的舆论环境。
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的比尔。盖茨的街头小贩创业实践会不会被城管扼杀在摇篮中?与硅谷的车库创业文化相比,在一刀切式的“民宅禁商”政策下,北京、上海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会不会因寸土寸金的高昂房租而倒下?公司稍有规模,面对形形色色的“赞助”电话,你如何说“不”?面对工商联副主席或政协副主席的可能邀请,会选择“商而优则仕”吗?……
鲁迅先生早就强调过“做土”的重要性:“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正是由于创业环境的差异,硅谷的创新型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催肥”下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而中国一些颇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士丹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
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和“复兴”。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大企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而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的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