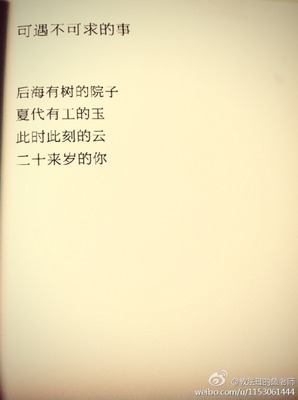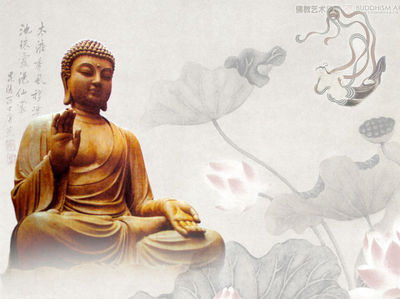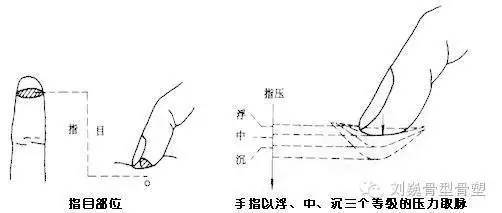在“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这个热点背后,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深究:第一,余秋雨为什么至今还这么热,第二,由谁来决定谁是大师。第一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他的热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很少有一个媒体红人能保持这么久的关注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之所以热,一方面与不断有让媒体炒作的新闻诸如“含泪劝告”等事件有关,更重要的是,余秋雨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大师”,他是当代作文的“大师”。
余秋雨的现代作文典范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套应试制度,与过去的科举制度相似,特别是作文的考试,它并不要求文章写得有个性,而是要求作文符合某种规范,这种规范存在于任何应试制度的时代,历代的科举考试中都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范本,然后为后世学子去仿效,这就是所谓的范文。
中国的这套应试制度是从1990年代开始被强化的,我觉得1980年代还没有这样。余秋雨的红与此有关。应试作文需要一个范文,某种文体成为整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一套作文范本,我发现余秋雨提供了这种范本,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大散文”,如今大散文成了中小学生的作文范本,余秋雨的散文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范本,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杨朔的《荔枝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毛泽东时代作文范本之两大代表。它们背后都有一套宏大的叙事,任何一个人物和事件最后都要归结出一个立意所在。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很难再重复杨朔、魏巍的那套宏大叙事,就在这个空白的时候,余秋雨出现了,他创造了大散文,这套叙事也是从小的人物与事件着手,但它最后要被归结、拔高到某个立意,那个立意即所谓的“人类大文化”或“民族大历史”,通常会运用一些大的概念来显示其意义的崇高。其中也不乏煽情之词句,用一种文艺腔加以修饰,形成从中考到高考的作文标准范式。
今年上海的高考出现了被一致叫好的满分作文《他们》,这是一个标准的、余秋雨式的“大文化”作文,这个范本看起来似乎有文化、有感伤、有关怀,但整个基调是千人一面的,它没有个人真实的情感——即使有的话,也已经被标准的宏大叙事和宏大情感内在化了——只是一层涂在劣质面包上的奶油。它更多是一种叙事与修辞的姿态,从小学开始,它被拆解为一系列技术性的手法,包括如何写景、写心情、写氛围、写立意……一切都是可模仿的、甚至是可以打分的。余秋雨之所以长盛不衰,我想这与他是“现代作文典范”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大师”,大概可以当之无愧吧。
只要我们还有这套应试制度、一套所谓标准化的作文,那么,就会有余秋雨的市场,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余秋雨的替代者。易中天是一种更适宜阅读市场和视听市场的时尚文化,他与主流意识形态无关。而余秋雨,则是世俗时代非政治的、被文化包装过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这套主流叙述里面有历史感和人情味,但历史感是政治正确加学术正确的集体记忆,其人情味也非自然流露的个人情感,而是一种人造的、标准的催泪情感。教育部门给余秋雨一个“大师”的称号,对他也是恰如其分不过了,当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余秋雨。
大师由谁来决定
大师当然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称号,但问题在于,谁可以来决定谁是大师?这次“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决定的,从这个事件本身可看出,今天我们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如今在教育界有各种各样的“名师工程”,这些“名师”乃至“大师”,它的决定过程不是竞争性的,而是由行政意志遴选出来的,或者由学校提名,或者由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它没有广泛的参与性及竞争性,很难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价。一旦公布以后往往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这次“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事件,除了他本人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之外,与这样一套遴选大师的程序不透明、不公开也是有关系的。今天的问题在于,体制中的各种名誉及称号,与社会舆论、学术界同行的标准差别太大,甚至形成了双重标准,两张名单。这两张名单之中,大部分的名字是不重合的。由此可见,由行政意志决定的“名师”、“大师”是如何脱离文化界、知识界和社会舆论。
人文学科领域的大师仅仅是一种美誉,是由社会舆论、特别是同行的公认所形成的美誉,大师并非是严格的学术称谓。达到大师境界的皆凤毛麟角,它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公认度,很难由某一个部门来决定。“大师”这个词如果是当面恭维,显得有点肉麻,甚至带反讽意味,假如自称大师、或者欣然笑纳之,那只能说比肉麻还不如。通常意义上的“大师”是指在某位大家过世后的若干年,他的作品和着作成为了经典,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因而被后辈尊称为大师。很少有一位大家在世时,就被称为“大师”。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同时代人封的,只有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留下了经典,才无愧为此称号。所谓的经典,一定是经过长时段的时间考验,不仅为同时代人接受,而且为下几代人所供奉为人类文明或民族文化的公共精神财富。没有一个经典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定为“经典”。比如在民国时期,今天我们公认为大师的,比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也是到他们过世之后,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才被海内外共尊为“大师”。而当年以“大师”自居,曾经流行一时的文化闻人,早就大浪淘沙,不见了踪影。
在我们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都在通货膨胀,到处充斥着的“大师”名号也在贬值。“大师”被权力和市场所操控,用“大师”点缀政绩、用“大师”包装文化商品,制造卖点。“大师”如今成为一个颇具反讽性的笑柄。而真正的大师,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师是不能被培养的,不能用某种人为的方式来制造大师。如果要有大师,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一个针对所有文化人的普遍氛围:给文化人更多的自由,他们不必“为稻粮谋”。活得比较体面,在社会上有起码的尊严,允许他们有各种怪癖、奇思异想。这样才有可能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之中,不期而然地冒出几个大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