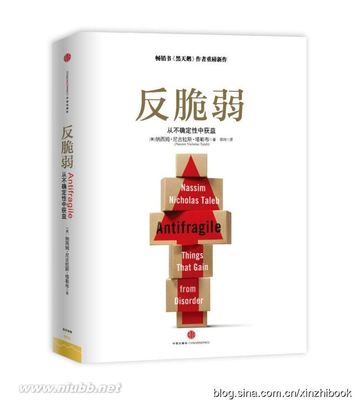9月14日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开幕,而6月建筑金狮奖的获得者就已提前揭晓。被誉为“建筑界的毕加索”的法兰克·盖瑞荣膺这一奖项,将这一奖项颁给素以奇思妙想着称的法兰克·盖瑞,其实就昭示了本届双年展的风向,“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 (Out there Architecture Beyond Building)。这个主题反复强调了建筑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而中国的建筑师们则一反各国建筑师求新求变的风格,着眼于现实。中国馆的主题是“普通建筑”,分主题是“应对”和“日常生长”,出于对5月汶川大地震的危机应对,建筑师们强调了如何在最脆弱的情况下使建筑功用发挥到最大。几个主要建筑师的作品——再生砖、支架栖所、集水墙几乎都是对地震灾后应对方式的展示。
而中国馆的另一个分主题,“自然生长”,则尤其强调建筑与日常生活和谐生长,反对权力对自然生长的阻隔。
实际上“普通建筑”这一概念有相当强的现实指涉性,但是似乎与整个双年展的主题背道而驰,策展团队没有过多涉及建筑的未来可能、建筑所可以完成的更美好世界这一主题。

关于中国馆在威尼斯展出的现状和反响,我们连线正在威尼斯现场的策展人龚彦以做了解。
《21世纪》:中国馆各项作品展出的反响如何?各方有哪些评价,认同的主要是哪些,而遭遇到批评的又是那部分?在认同和批评之间,可以看出哪些观念上的歧异?
龚彦:由于在这次双年展中,大部分展馆选择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建筑和观念,比较少选择实物搭建的方式,所以中国馆的展出是相当突出的,甚至显得突兀。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建筑观念上的普遍审美和基础都已具备,人们追求更形式更感性的东西。而中国的现状尚无法达到这个高度,因而采用实物搭建的方式,反而比较容易反映中国的现状。
实际上一开始就有人说了,我们这次的策展主题和双年展本身完全是个反的。很多人非常诧异我们会以普通建筑为题,他们以为会看到类似于迪拜或者奥运那样宏大鲜亮的展示。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次参展的目的并非展览本身,而是着眼于展览之后能够对国内发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将着眼点放在中国建筑的现存,而未作过于前卫和先锋的探求,从国际范围来看,我们国内的建筑才刚刚起步,我们需要立足于本土,我们希望的是展览后对国内的影响。我们的心态主要是透过一个国际交流平台看清自己,因而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没有选择明星建筑师,因为他们更多从外部、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我们选择了三类建筑师:院校的老师、国家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做古建筑文物复原的建筑师。他们是真正会对中国目前的建筑现状起到作用的建筑师。
在展览中,很多我们接触到的西方人非常惊讶我们以普通建筑作为主题。他们对分主题中的摄影展感受很深,在威尼斯军械库油库的摄影展布展简单,照片平放于办公桌上,接近阅读的经验,从中看到代表中国某个阶段中国人的心态,在这么一个国际大舞台上,我们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展露出来,他们觉得非常诚恳。
《21世纪》:那么是否遇到不同观念的碰撞?
龚彦:很多人看建筑的角度不一样,这里一个很大的趋势是显现未来。西方的主场馆表现了很多老牌的未来主义,比如蓝天组,也邀请了12位设计师展现未来的城市。有一部分媒体着眼于未来,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展馆,会觉得特别朴素。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既表现了我们当下的处境,也体现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都说这不是一次展览,而是一次真实的还原。
《21世纪》: 好几个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其实体现危机应对的观念,甚至主要集中在应急材质上,这在建筑观念上究竟有何推进性的意义?这些应急材质在现实使用上的可行性高吗?还是说以体现观念为主?
龚彦:有一部分完全在实行了。比如刘家琨的再生砖。已经完全投入了使用,在灾区居民翻建住宅时,很多地方都在采用再生砖。这种再生砖成本低,制作简单,很多都是当地农民自己造的,解决当地一部分人的就业。再生砖在展览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21世纪》: 我们可以看出在“普通建筑“这个观念中,其实隐含对权力的批判,尤其是对阻断自然生长的权力的批判,但是在实际作品的展出中,我们感觉这种批判的力度是不够的,甚至隐而不现。你怎么看待?
龚彦:权力渗透在艺术结构之内,是无处不在的,很难做到可视化。实际上仅仅就是在整个中国馆申请批文、策划、搭建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对权力的平衡。最开始是不是做一个中国馆,都在批文上遇到过困难。因为中国馆一直被称为临时馆,在这么一个最高级别的 双年展中,全世界有五十多个国家的独立展馆在这个舞台上,而中国现在还只能占据一个临时馆,因此从2005年能够开始是很不容易的,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体现了非常有包容性的文化姿态。今年是奥运年,在西方媒体过度的政治关注之下,中国继续愿意走出这一步,更体现了包容性。比方策展人之一的阿城是体制外的,中国馆能够包容他,让这样体制外的人发声,谈出对中国现状和过去的看法,都非常宽容。建筑就是某种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体现,在这次双年展上也可以一窥究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