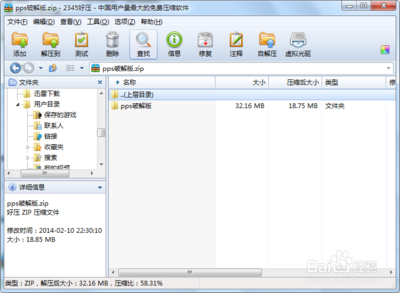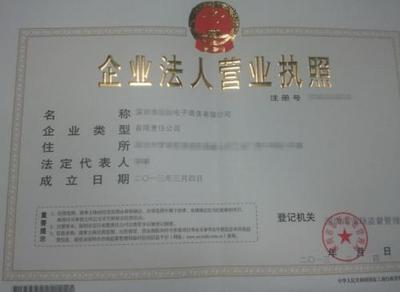这是一座座岛屿组成的社会。说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一脸茫然。社会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成员在其中相互往来,即便存在地理上的间隔,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孤岛。倘若你生活在过去的农村,也许的确不孤单。乡土社会的一大特色是,看似一个个孤立的村庄,生活着不同姓氏的人们,但这些人相互之间却是密切关联的,这种社会链接可以表现为血缘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友情的方式,还可以表现为同是农村人的那种质朴的情怀。 但城市就没那么幸运了。城市是有着严格时间限制的工作场所。工厂按时上下班,人们不是在单位里,就是在家里。社会交往至少在时间上就很受制约。城市越大,社会交往的成本就越高。不过这些都不是关键因素。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把每个城市人的身份单位化了。张三属于甲单位,李四属于乙单位,如此等等,因为单位的存在,张三和李四都有了某种社会化的符号。这种社会化的符号原本就是社会角色的体现,但由于单位的背后隐含着资源、权利、地位、居住和收入,于是单位就成了某种不平等的催化剂。说起来社会成员是人人平等的,可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过得好与过得不好,取决于你在什么单位。单位把单位里的成员人为地划分成了不同类别,再加上家庭成分制度把人界定为三六九等,于是单位和家庭成分就构成了城市人归属不同等级的标准。在这标准下,原本平等的城市人就被划分为不同岛屿的人,城市也就演变成了孤岛结构。改革前这种孤岛结构是触发社会冲突的一个关键,只是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 改革之后家庭成分制度被废弃,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使得城市人的流动性增强,城市孤岛的格局一度被打破。孤岛之间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增加而逐步密切联系起来,从而社会资本也开始逐步增加,这大概是支撑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我们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看到市场化本身可能反过来阻碍这种流动性!市场会毁灭市场,这大概是某些对市场极端膜拜的人所想不到的。市场怎么会毁灭市场?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引导,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人群分化和社会隔离,从而导致市场化无法持续。很多人都迷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却忽略了这只手要真的给社会带来持续的福利改进,需要每个人各方面都一样,且每个人能够平等自由竞争。而恰恰现实社会不遂人愿。人生而不同,能力、长相、家庭背景等等,都伴随一个人的出生而表现出千差万别。即使一开始社会能够自由平等地竞争,当一部分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精英,而另一部分人竞争失败,成为社会的底层时,自由市场也就等于一句空话了。这是因为处于顶层的人群会更有能力增加自己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入,并能够通过自身的垄断势力来阻碍底层的人往上流动,于是社会阶层会固化,这就应了那句古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倘若没有恰当的公共政策,市场只能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会导致不自由和垄断。再进一步设想,倘若公共政策不是去矫正市场的局限,反而对不平等的后果推波助澜,那么代际不平等会因不好的公共政策而强化。改革开放30年,忽略了一个公平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的设计,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本身就采取了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使得原本社会成员可以平等共享的公共资源现在只能被少数群体重点享有。这样一来,非但公共政策没有起到矫正市场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把城市解构为一个个岛屿。这岛屿虽然和过去那种单位与家庭成分的划分不同,但本质类似。收入、地位、财富和权力构成了城市岛屿的四大特征,这四项中某项或者四项都较高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较高水平的岛屿,而其他人则形成各自的岛屿。岛屿之间因为代际不平等的事实而难以流动。于是乎我们看到,城市岛屿的形成再一次降低了城市的社会资本,从而可能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发展。所谓转型,理应设法通过重新设计公平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来打破这种岛屿社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