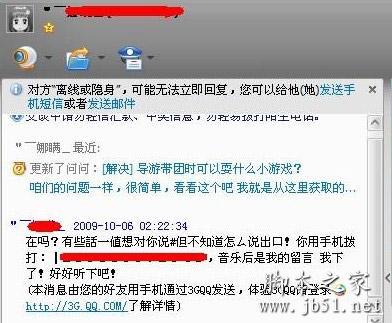传统观念认为公司是一个大的经济实体,其首要任务是回报股东。这种前提一旦受到质疑,往往是出于道德或政治的原因。“公司不但要为股东负责,而且还要为员工和社会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论点。阿里·德赫斯却另辟蹊径:公司的忠诚对象不是任何一个股东,而是它自己。一味追求利润的公司不会学习,因此,它们不会繁荣,甚至不能生存。
德赫斯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的事业生涯主要是在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壳牌(Shell)集团里渡过的。1988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学习中计划”的文章,使其成为著名的管理思想家。在这篇文章里,德赫斯提出,不断对目标和方法进行重新思考,这一能力对于公司运作不仅是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且是取得竞争优势的惟一因素。公司的财产可以贬值、创意也可以被窃取,但是,只要他们拥有创新和发展的能力,仍然可以一马当先。
德赫斯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有生命的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公司目的的新观念:公司应该被视作生物有机体,按照有机的步骤成长,这样,公司的寿命就会大大超过其他的竞争者。这意味着再也不能把公司当作榨取利润、回报股东的机器。新经济的退潮证明资本已经成为一件商品,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筹集资金,而是招募、留住和配置优秀的员工。以下是对德赫斯先生的访谈。
问:在《有生命的公司》一书中,你提到将公司看作一个生物体,按自然的方式进化,为自己的长寿着想,这是最有效的公司思维。在传统观念里,人们把公司看作纯粹的经济结构,目的是为股东返还投资,你认为这种看法不仅不对,而且短视,导致了很多公司昙花一现。我们刚刚经历过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次是互联网公司垮台,这对你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我不敢断定亚洲危机对我的理论所产生的确切影响,但是,dot-com泡沫令我确信将公司看作生物体是正确的。
我在《有生命的公司》的开头,描述了一项80年代在壳牌集团进行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公司中,至少有45%的公司历经创造性毁灭而生存下来,有些还存活了几个世纪,而《财富》500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0年。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公司把重点放在诸如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特性上,再结合上追求利润的实用目的。长寿公司不会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企业主和股东追求利润和价值的经济体,他们认为自己是另外的生命系统——由为他们工作因而也属于他们的人所组成的生命系统。
问:那么dot-com公司有什么不同呢?
答:很多新经济公司似乎以这样的理念为出发点,即他们是十足的经济实体。我最初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似乎与这些公司运用创造力的商业目标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这些公司迫切需要高水平的知识和创新,但是他们却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来进行组织,而后者是19世纪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Dot-com公司的管理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输入人才是公司成功的惟一源泉,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股票分给重要的员工,让他们参与到尽快赢利的游戏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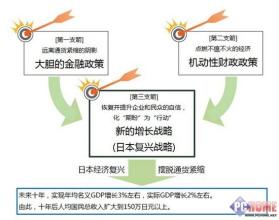
问:人们一直认为,让员工与公司的目标合二为一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这种激励机制。
答:一旦你参与了游戏,最终的股票价格就会成为衡量你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在早期阶段,dot-com泡沫制造出了一大批富人,在35岁就实现了一切,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却只有死路一条,包括那些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这些公司上的人们。过去的一年半时间,让我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长期繁荣的公司又是怎么做的呢?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自80年代后,公司最需要培育的资源发生了转变,从资本转向了人。一个公司的成功不再依赖于筹集奖金的能力,而是依赖于人们的知识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next]
问:能举个例子吗?
答:今天,在《财富》500强中,持续增长的公司——思科、微软和EDS——的固定资产相对较少。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较高的股票价值与较低的固定资产价值间的区别表明,智力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答:几年前,你去参加一个经理会议时,不可能听不到人们在谈论“可雇用性”,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你能为我们工作一段时间,当然了,我们不会与你签订终身合同,那是日本人的做法,我们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毫无疑问,在你为我们工作两年后,或者你想走,或者我们想让你走。但是这对你并没有坏处,你取得的经验会提高你的可雇用性。”
在这样的推理背后就是拒绝。你招来的新人实际上与公司的职业社会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可雇用性意味着公司根本就没有人,它只是一架造钱机器。从这种意义上讲,“可雇用性”现在完全不被提倡是一件有趣的事。
问:这是怎么发生的?
答:几年前,我在与几位来自软件业、金融服务业和咨询公司——这些都是“可雇用性”一度流行的地方——的人交谈时,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变化。人们对我说:“如果有人为我们工作四五年,并且在组织中取得了资历,那么如果我们失去这个人,就等于失去大量的金钱。”我记得三年前,甲骨文公司的一个人提到过,更换一个在公司里工作了五年的人的成本是50000至60000美元。因此我开始调查其他的上升公司,有些咨询公司说如果他们失去一位资深顾问,就会损失200000美元和18个月的业务。
问:这些成本都包括些什么?
答:包括招人的费用、培训的费用、更换合同的费用、弥补离开的人带走的专业技能的费用。在人的问题上,公司真正应该重视的不是“可雇用性”,而是如何留住他们。因此,持续性再次变得与基本的商业原则一样重要。
问:一个天真的问题:如果持续性和留住员工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人们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
答:这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把公司当作造钱的机器。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法律提供了相当多的便宜条件。
比如,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法根据的都是这样的前提:股东拥有公司。这种源于过去的概念强调资本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它为资本提供者赋予了两项特权:首先,股东对公司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可以决定由谁来管理公司;其次,股东对结算享有极大的特权。公司在法律上有义务为股东返还利润。即使股东并没有为公司注入直接资本,只是从另外的股东那里购买了股票,同样也要享有这些权利。
但是,因为今天的公司完全依赖于内部成员所提供的智力产品,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在结算上出现分歧:利润首先应该分给那些所谓的“股东”,还是应该分给公司内的成员?
在新创企业中,这个问题相对平和。创始人把他们最初的小型合伙人公司转换成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可以发行股票并分给自己的员工。直到员工把自己的股票在公开市场上出卖,或者出售给风险投资公司,在此之前股东和公司员工间不会出现利益上的分歧。[next]
问:可能是在他们退休的时候。
答:或者他们需要钱的时候,或者他们想买一艘新游艇或一幢新别墅的时候,高层的员工最有可能这样做。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股东们要问:这个公司真的做到让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了吗?当公司外股东想要运用他们的权力——要求公司如何运营,或者提高自己的收益率——时,他们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当股票集中在大的股东集团——风险投资商、保险公司——的手里时,就变成了与公司管理关系不大的金钱游戏。
因此,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新创企业中,还是在高盛这样的公司里,在发展的要求和留住员工的愿望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而且这种压力正来自合法的股东们。
问:你的意思是,现在流行的公司管理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你是否暗示,忽略大股东要求的公司从长远看会挣到更多的钱?
答:我还没有走到这么远,但是我认为在股东与公司员工间确实存在着冲突。股东说:“我有合法的结算权。”而员工们说:“嘿,如果没有我们的才智与知识、我们的智力产出,就根本没有结算这一说。那么,我们的报酬又从哪里出呢?”
我可以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情况。
在上个十年里,欧洲许多足球俱乐部都抵制不住诱惑,将自己变身为有限责任公司。但是为了成功,各俱乐部不得不花额外的钱去同球员和教练签约,只有他们才能实现竞争。结果呢?在欧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俱乐部公司在财政上能够支撑下去。每个俱乐部都有把它看成是造钱机器的股东:他们投钱就是为了收钱,但是无钱可收。
问:因为钱不够周转?
答:对。股东们通过结算撇去了利润,但是教练说,“我需要2000万英磅来购买两三名球员。”否则就无法带来结果。因为如果不能把球迷吸引到球场,球迷就不会买T恤之类的东西。当股东和教练发生了这样的冲突时,教练的立场更为有力。类似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其他形式的企业中。
问:这种冲突是否是管理与股东矛盾的另一次循环呢?比如80年代就曾出现过。
答:80年代是这个转换时期的开始。那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人的知识和能力成为关键要素,但还不足以影响到公司的管理。
今天,我们面对着更深层次的转变。现在的资本市场是买方市场。资本和小麦一样成为了商品。如果真是这样,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陈旧的资本主义组织概念就不再有效。
问:这种转变的受益者是谁?
答:那些在特种行业中拥有过人才智的人是最早的受益者。在好莱坞一小群电影明星能挣到2000万的工资并非巧合,在体育界,报酬也流向了那些具有出众才华的人。[next]
问:那么,像壳牌集团这类公司如何应对呢?
答:在每个感觉到要为明星员工付出额外报偿的公司内部,都要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能够取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明星员工还是团队表现?壳牌集团仍旧没有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因此他们在处理诸如红利和奖励这种事情上非常谨慎。
问:这是否意味着壳牌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他们必须要做哪些与以前不同的事?
答:壳牌集团已经开始从外部招募高层职员,他们以前很少这样做。现在,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争论,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企业的成功完全可以通过雇佣一两个明星,并给他们超出想象的报酬来实现,但是很多公司不会这样做,他们仍将追求团队表现。
问:会不会出现一种注重明星员工的趋势呢?
答:长期繁荣的公司几乎都是那些没有面孔的公司,比如壳牌集团或者英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外人根本说不出他们的CEO是谁。但是,这些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他们要学会优化人,而不是资本。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做到让自己员工的才能最大化,确保人才的来源并留任人才。这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巧,比起维持资本供应,也可称为更困难的技巧,目前惟一有效的方法是在内部开发人力资源,关注员工的成长和愿望是公司管理人员的首要任务。
问:发生在开发人力资本中的这种变化对公司外部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们正在进入的世界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在今后几年,财富不平等的差距将会拉大。所有的国家,如果不为人口的潜能投资,一定会输掉未来。有些国家可以筹到资金来修建一座汽车组装厂,但是他们的汽车设计、制造方法或者市场手段永远也赶不上日本、美国或者欧洲。
问:你认为这些国家永远也赶不上已经成为领头羊的国家了吗?
答:是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比方说,如果中东国家继续将妇女排斥在体制之外,很难看到中东会赶上美国、加拿大或者欧洲,因为有一半人口的智力资源白白浪费了。
但是收入间的差距还会创造出一种我们不熟悉的社会紧张形式,如果你是生活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穷人,你仍旧有一种归属感。但是,如果在你生活的社会里,荣耀是与教育、成功、才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你从来就没有分享这一切的机会,那么这种贫穷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你对社会的感觉也会完全不同。
问:有没有公司正在面向未来、做好准备?
答:在美国,有一群建筑师找到了我,他们阅读了《有生命的公司》并按照书中所讲的原则组织了自己的公司。当然,我们在80年代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的长寿公司在新世界中取胜的机率会很大,他们把从过去带来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经济现实进行了整合,相信成功依赖于人的才智。旧赢家成为新赢家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你仍把公司当作一个有限责任组织,并在商学院中被效益和资本投资回报率洗过脑,那么转变思维,将资本视为次要角色并不容易。但是,我看到传统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的商业现实是以人为核心的。他们看到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是比对手产出更多的智力产品。他们意识到只能通过让人们学习、提高凝聚力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让他们像机器一样提高效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