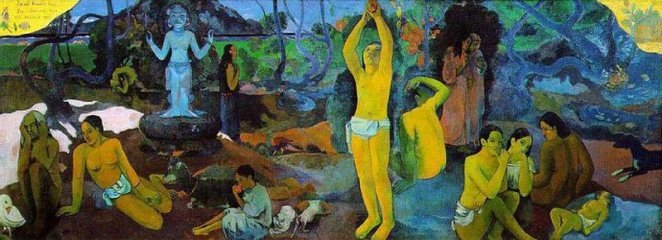刘庆云出生于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88年赴日本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在日20年,刘庆云从在日中文报刊转入电视电影界,主要为日本NHK等电视台制作中国题材的电视专题纪录片,参与从节目策划,审批选题,现场采访,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10余年来,作品数十部,通过日本的主流媒体把真实的中国传递给日本观众。 时代周报:《麦客》获得了大奖? 刘庆云:实际上,后来我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120分钟的高清版本,像电影一样;另一个50分钟的版本,在综合频道播出,每星期日晚上9点黄金时间播出,这是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金牌栏目,叫“NHK Special”(NHK纪录片精选),这个特集是日本纪录片第一名牌,很多电视人将能做“NHK Special”当作人生梦想,它可谓是纪录片的最高峰。 《麦客》播出后,影响很大,获得了ATP电视奖,这是由全日本电视节目制作社联盟主办的每年一度的评奖。由三个部门—纪录片、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分别评出当年度最高奖。《麦客》首先获得纪录片最高奖。最后在颁奖晚会上,再评出最大奖,在三者中再选出一个,即ATP奖。当时现场气氛很热烈,三个灯光向上升,先是综艺的停下来,然后电视剧的停下来,纪录片的还在向上升。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是在2003年。一般来说,电视剧、综艺节目获奖的较多,但《麦客》获奖却是众望所归,而且票数高出不少。它同时还获得了摄影奖。后来,《麦客》成为NHK纪录片的经典,很多日本导演都知道了:割麦子的。 在NHK的高清节目20周年之际,做了一个优秀节目展播,一共选了7部影片,1个星期,每天播放1部。其中有两部是我做的,另一部就是介绍日本遗留孤儿、后来成为日本最著名漫画家之一的千叶彻弥,回到沈阳寻找中国恩人的故事:《我心之旅—阁楼上的日子》。 时代周报: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庆云:这个节目拍完后,导演感叹,到中国来拍片题材简直太丰富了,如此情节,根本不需要去编去导什么,直接拍下来,就足以感动观众。 回日本做节目就没什么兴趣了。在日本大多数节目比较平淡,因为没有这么大起大落的历史、现实。在日本,民族单一,生活相对平稳,时代的变化是缓慢的,人物故事没有太多离奇和曲折。这也是促使NHK拍摄这么多中国题材的原因。每次拍完,他们都感叹,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么精彩的故事。 中国题材之丰富,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国家能相比。恐怕唯一例外是俄罗斯,你看俄罗斯的小说、绘画,历史凝重感非常深厚。但NHK没有拍摄那么多俄罗斯的,因为中日之间文化的关联太紧密,距离又很近,现代经济上日本更加离不开中国,蔬菜80%以上从中国进口。加上战争,中日之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民众对中国的关心度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关心度要高得多。尤其是经济上的关联,让更多日本人和日本企业需要更加了解中国。 时代周报:NHK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 刘庆云:改革开放之前,对外媒是封闭的。只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共产党和中国有过一段时间交往,那一时期日本的电视台也到中国来拍过反映“文革”题材的纪录片。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数量已经超过5000部,而中国中央电视台到日本去拍摄的纪录片只有一部:《岩松看日本》。

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座时,和日本学生交流,讲到了上面的数字对比。日本学生就提问,为什么中国对日本的关注这么低?我也不客气,说:很抱歉,应该这么说,日本离开了中国,活不下去,或者是活不好;但是也很抱歉,中国人没有日本,也活得很好。这话很刺耳。当然,我是希望中国的媒体能制作反映当代日本的纪录片,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日本,近些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很多是因为不了解甚至误解。缺乏沟通缺乏了解,令中国民众认为日本人都是反华的。我就想,多做一些反映中国的纪录片给日本的观众看,让日本观众了解到,中国民众对日本是渴望了解的,希望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