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在今年六月初的上海做了一次演讲,那是一家民营美术馆新馆开幕,他演讲的主题是“民主风尚与艺术天赋”。彼时正是“国父论”纷纷扰扰之时,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却对前来请教哲学问题的青年学生们“亲切有加”。 除了刘小枫等为数不多者,上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的“青年导师”们如今早已消失在公共视野中。 至于一些仍然活跃者,依然还在用“惊世骇俗”的老策略。 “惊世骇俗的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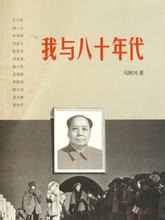
已经不太有人记得上世纪80 年代初那一场卷入了三四千万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大讨论。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里问的问题是,“我整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 1980年6月《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开始刊登来稿来信讨论潘晓的追问,这个讨论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从1980年6月到12月。潘晓的追问在千千万万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共鸣,据后来的资料披露,《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得用几个大麻袋接收这场讨论的读者来信。 “可以说,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人的共同问题。1978年改革所确定的方向,使得人们一时间丧失掉了精神寄托,此前确立的人生意义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青年一代尤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断裂与意义危机。”《开放时代》杂志曾做过一次有关80年代思想界的论坛,当时的杂志主编、现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做了这样的解释。 “青年导师”们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为年轻一代的人生意义、精神寄托找到了归属,并最终促成了当时的“文化热”。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 刘小枫是其中颇为年轻的一位。1988年,继《诗化哲学》一书之后,刘小枫以《拯救与逍遥》引起轰动,扬名学术界。一时之间,他成为众多学者、学生的偶像或“精神初恋”。再后来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与其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纷纷远走异国的人不同,刘小枫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一位亲历过那个年代的教授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精确地说,由于80年代以前,中国思想界处在一个跟世界文明唱对台戏的状况,比如人道主义是坏东西,人性是坏东西,然后完全去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教条,既可以说是一片荒芜,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片黑暗,所以80年代作为异军突起,要把它说是一个高峰,甚至是出现了一点小小文艺复兴的迹象,其实并不夸大。” 在他看来,无论刘小枫还是李泽厚,他们的观点相对于以前的历史背景是大胆新奇、标新立异的。“但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了解西方哲学的人来说,许多东西在西方完全是常识,毫无新颖性,但在中国就是惊世骇俗的,所以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攻击。举个简单的例子,李泽厚提出: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愿意选择康德而非黑格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不着提的东西,在西方是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但在中国就是大逆不道、惊世骇俗、引起群起而攻之的东西,他们能欢迎和接受西方的常识,敢于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一个‘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导师。” “时代赋予的任务”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引发了思想文化的相应转型。80年代的“青年导师”们开始逐渐退出舞台。 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他后来对90年代思想界做过这样的归纳,“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更多的是将原因归于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成为主流,让大众开始对思想、学术冷眼相看。不过,李泽厚也坚持,时间可以检验作品的优劣。 也有学者分析,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中心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公正问题牵动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兴趣也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关怀转向了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原理原则,从人文修养转向了社会科学。而“80年代的理论家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问题上缺乏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学界普遍认为,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有巨大的超越。“青年导师”如李泽厚,其学术地位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并没有因大众视野的缺席而消退。追究原因,恰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讲,李泽厚“不是研究某一种哲学的,而是一个以生命从事哲学活动的人”。 一些“青年导师”的作品在90年代被重新评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出版之时,何光沪、宋一苇等学者曾予以高度评价。在何光沪当时的评论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在我国,国民自我局限久矣,学人自甘有限久矣,思想界自陷于有限的实证经验久矣!因此,小枫这本追求自我超越、指向超验价值的书,可说是对这种现状的沉重一踢,而书中的种种缺点或瑕疵,倒像是加重这一踢的粗糙马刺。” 到了90年代,评论家夏中义在对这本书的重估中,放弃了该书刚刚出版时获得的简单好评。有评论者分析道:“经过夏中义的学术重估,研究者会发现,《拯救与逍遥》并不像80年代评价的那样简单,仅仅是用宗教来拯救国人。它是在当时实用主义的误读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是为了拿来就用。” “8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为经济、政治改革开路。只有理解了‘借谈文化讨论政治’这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目的,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谈问题,恰当估量80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如果脱离了这个语境,以中国近代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参照,那么我们根本没有‘思想的创新’可言。以纯粹思想看,80年代大陆主要思想领袖、文化英雄的重大贡献其实借鉴了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的观点,也谈不上有多少思想的创新。”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说,他的评价只能限于“时代赋予的任务”这一维度,“而不是以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纯粹思想学术的标准”。 面对近几年来刘小枫所引发的争议,以及邓晓芒与刘小枫之间的论战,这位教授的观点是:“邓晓芒要证明刘小枫引进来的东西是不对的,学术价值不大,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早就有公认了。但是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意义却很大。因为,刘小枫在中国学生里面的影响依然有,他引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对于青年人的毒害是很深的,而一般人又不愿意把问题说破。从这种意义上,邓晓芒是出于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说这件事。”他甚至将邓晓芒类比于当年的“青年导师”的工作—将一些原有的谬论,做一次正本清源。 对于当下的一些学者来说,一些人不再是青年学生的导师,“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中国进步了,整体水平提高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