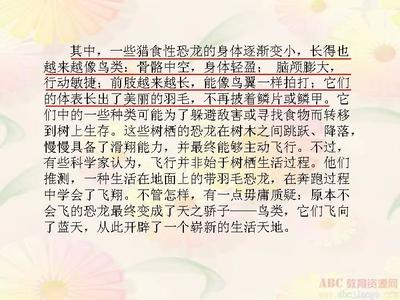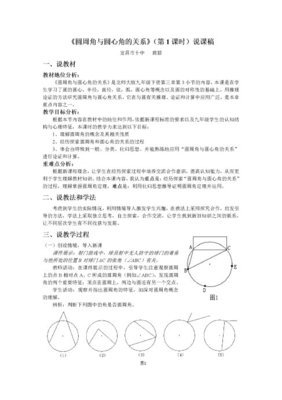2006年春节前,我在一次上海媒体聚会上,见到了原太平洋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当时他极力推荐我加入太平洋,并对我说:“听说老严要打造南京、上海、北京三个集团,现在上海这边前期筹建事情很多,又要应对各路媒体,太缺合适的人才了,南京文化部这块可一直是老严最重视的。来到上海,更是需要有人帮他管理和运作文化宣传。”当时,严介和对第一财经日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本书后面会提到,他的三大媒体硬伤,也就是媒体给他带来的负面冲击,第一个就来自于第一财经日报。在这之后,严介和也通过文化部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说起太平洋准备来上海的一些想法。说实话,如果加入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所在的公司,不仅我心里没底,我的媒体同行也表示出了担心。听说了我要离开报社的消息后,时任报社副总编的张庭宾和财经中心编委杨燕青两位报社前辈找到我并诚心诚意想挽留我。最终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换位体验一下这种位于媒体风暴中心的企业最真实的感受。

应该说我从作为一名记者开始认识太平洋,再到进入企业内部做管理层,我了解到了与外界眼中不一样的、真实的企业现状。媒体站在外面看企业很多时候是雾里看花,而对企业而言只想展现其光鲜亮丽的一面。企业以为媒体是传声筒,总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想借助传媒这个平台向外发声传话。但媒体是双刃剑,后面有提到,既可以扬声也可以变调。所以企业在很好地维护和媒体关系的时候,既要给予媒体适度的报道方向的引导,掌握好消息披露的原则和节奏,也要懂得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和行业规则。同时企业对待媒体的态度应该是真诚的,说话应量力而行,不能过度。如果说的话变来变去,随心所欲,前后口径不一致,必定会失信于媒体。上胡润榜给严介和带来了名声,当然也给他带来了大量工程订单。但如此庞大的订单都用严介和所谓的BT模式运作,都是需要资金做后盾的。所以,关于严介和成立苏商的目的,媒体也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因为严介和想转移太平洋资产,有的说是为了融资。严介和则公开地讲,“上海苏商就是一个融资平台,它成立以后可以解决太平洋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上海苏商成立以后的发展轨迹让严介和有些失望,他并未从南京带来一兵一卒,苏商的人员都是在上海本地重新招聘的。苏商的成立并没有按严介和想像中的那样迅速为他带来现金流,而上海过高的商务成本也令严介和日渐感到吃力。来到上海本来是严介和在当时太平洋已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选择,但上海之路并未给严介和带来好的转机。严介和是多年来如此高调面对媒体的少数企业掌门人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也是影响他成败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企业和传媒的关系是我在这段经历中经常思考的一件事。媒体人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成功的时候锦上添花还是失败的时候痛打“落水狗”?企业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媒体,是利用媒体达到成名成家的愿望,还是三缄其口、回避媒体、谈媒色变?虽然后来我和许多苏商人一样不得不选择离开公司,但我一直认为这段媒体聚光灯下的企业经历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这也算是我在“太平洋”这段不太平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笔“财富”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