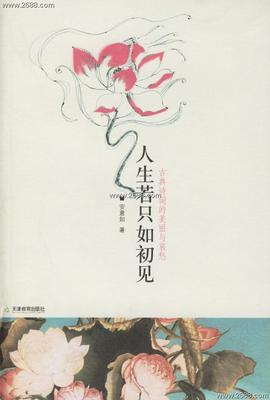50年前,一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引发了文学界空前的热情。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大师和文学经典的敬重,似乎让中国文学界看到了希望。然而50年后,正值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中,却显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多是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作为中国经典名著,是它的艺术价值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审美标准,抑或是对于红学文学艺术的传承已经出现断代? 二月河:文学创作要研究历史真实性 问:《红楼梦》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加入真实的历史。你的小说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加入虚构的情节。在文学创作中,艺术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怎样做到融合? 二月河:我在创作过程中,讲究两个“真实性”。一个是历史的真实性,一个是艺术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进行双重的整合。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历史时间的真实性。例如,《康熙起居录》对皇帝的日常生活都有记载,从起床、更衣、如厕、进膳,吃过饭以后接见了哪个大臣,说了什么话,气氛如何等,都有详明的记载。但并非说把这些翻译成白话文,就能成为《康熙大帝》,这个反而不真实。真正的文学创作,是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总体的政治生活、人文生活,乃至于包括军事,要进行抽象,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工制作,让它变成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种写作方式,也是我模仿学习《红楼梦》的写法。《红楼梦》本身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真实,但里面的故事又都是虚构的。把当时整体的社会气氛渲染出来,以及阐述这种社会气氛下产生悲剧的历史必然性,这也就是它的伟大之处。 问:你从作家写作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和专业的研究者有什么区别? 二月河:正如我前面所阐述的理论,文学创作体现的是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全方位的了解,以及对整个社会生活细致的剖析。所谓写得活灵活现的小说,就是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但现在很多虚构的小说和电视剧,对这些都不去做深入的研究,那些场景虚构得特别夸张。比如我们常常看到有女侠客骑着高头大马,从市集上穿过,但如果深刻研究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种行为就好比现在你脱光了脊梁,腰里别一把大刀在天安门广场上晃,肯定直接被拿下。 所以,在文学创作之前,我主张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甚至一斤菠菜韭菜多少钱,他们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要有所了解。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可能会接近真实,完全真实也是做不到的。 张庆善:不能苛责年轻人抛弃了红学 问:你认为最近几十年最具现实意义的红学研究成果是哪些? 张庆善:我认为最大的成就在于,突破了过去很多思想禁锢,用更加开放的视野对于《红楼梦》进行了更多元化的研究。多元化的研究视野,使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对红楼梦的了解更全面、更真实。 以往,我们只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去认知和研究红学,在当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毕竟对作品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而如今,我们强调用立足本土的国际化眼光去审视红学。所谓立足本土,就是要坚守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学术规范、传统学术理念、传统学术文化;放眼世界就要用一种国际视野,不要故步自封,借用西方的理论谈红楼梦心理描写、谈红楼梦的叙述细节、谈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谈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当然也可以用中国传统理念谈一谈中国人的审美等。 问:你常常提到红学的现代传播,以及围绕红学的文化产业发展。但就我们所知,现在很多全国各地很多红楼文化产业园都经营惨淡,这是否说明红学发展方向与现代审美相背离? 张庆善:其实不能一味苛责年轻人抛弃了红学,作为红学研究者,我们也常常反思自己在推动当代红学传播的误区。现在很多关于《红楼梦》所衍生的文化产业也确实经营不善,这主要跟以前的发展思维有关,而并非《红楼梦》本身的文化价值会被否定。 以往红学研究甚至很多红学产业都是政府行为,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产业发展,是需要全民参与的。比如我们与新绎集团正在建设“梦廊坊”文化产业园进行合作,正是一种实践尝试,用企业的力量以及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去推动全民体验,发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研究文化,进而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全民效应不行,文化发展没有全社会的参与也不行。说到底经济发展首要的任务也是文化问题,真正讲到中国的经济要能可持续发展,没有文化的底蕴将来肯定要受限制、进入瓶颈。

二月河:中国大陆作家凌解放的笔名,著名的代表作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此举发端于他的“红学”研究。 张庆善: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