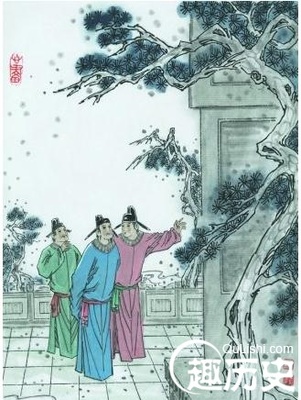合起雨伞,踏着电动扶梯到三楼。带位小姐把我和老妻领到靠窗的座位。头稍稍偏向右边,帘外,笔直的雨线,切割伞顶的半圆和候车站翘起的檐牙。共伞的人不慌不忙地走,高跟鞋的细跟勉强地和雨线维持平行。停车场的红砖格外地触目。 凝视雨网之际,想起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风马牛不相及,也许仅仅因为“餐厅”和“酒楼”是同类。另外一个暗示是:这是一家日本餐厅,店名“上野”。怪不得在街上走时这高挂在大厦外墙的招牌,教我想起鲁迅散文《藤野先生》的开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好在这里无樱花也无藤野先生的遗迹,若有,我这顿饭怕要吃成“文革”的“忆苦餐”了。 同是吃,“吃出什么”却大相径庭。鲁迅的《在酒楼上》,基调阴冷压抑,“我”和主人公吕纬甫,在S城的“一石居”巧遇,从头到尾喝酒,先是“我”独酌孤闷,再是两人共品颓唐。我和老妻,却是纯碎的“吃货”。打了一个上午羽毛球,回家做饭太晚,便决定在外面解决。酒楼上的两位读书人,以三斤绍酒浇无穷尽的块垒,什么油豆腐、茴香豆、冷肉、青鱼干,首先是酒的附加物,然后,和“主人”绍酒一起,成为道具。他们挂“喝酒”的羊头,卖“伤感”的狗肉。光是伤感,倒无伤大雅,这是一种从古到今并没有衰退的普遍心态。然而“伤感”的后面,是绝望。吕纬甫重新安葬早夭的弟弟也好,遵从母亲的指示,给乡下女子送迟到的剪绒花也好,如此温情脉脉,背后都是幻灭。 我们只是为吃而吃。乌冬面加配炸肉排,佐以微辣的红色酱汁。牛腩和生菜、绍菜、大蒜、萝卜滚热在小小陶锅里。向上帝坦白,如果没有联想,这顿饭堪称完美。而这完美,由恰到好处的饥饿酿造。 遗憾的是,吃到一半(从时间上推算,《在酒楼上》两个一点也不快乐的男人,这阵子该已寒暄过,并慨叹,上次别后,彼此都像少年时看到的小虫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肚皮填了相当多的乌冬,开始喝白得有点奇怪的汤,惊惶自问:是原汁原味的高汤,还是用比味精还厉害的新型调味剂调的?要命的联想一经启动,殃及别的菜:这炸肉排,从什么油里捞出来的?即便不是地沟货,如果店家为了省钱,油多天不换,炸出来的也足以致癌。还有加点的炸银鱼—我和妻子从来不吃油炸食品,今天自投罗网。 想起“打工皇帝”唐骏在演讲时,一本正经地说的故事:某优秀中学生在一次考试中大失水准,老师招他去问缘由。学生哭着脸说:“不能从小日本那要回钓鱼台,考得再高分,有用吗?”老师兴奋之极,拍拍爱徒的肩膀说:“好样儿!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唐骏说完,台下没人发笑。如假包换的国产黑色幽默。我独自偷偷苦笑,那表情,该和吕纬甫他们半酣时差不离。 要之,《在酒楼上》的吃,从“吃”自家的凄凉遭际到“吃”前途之无望,“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以“密雪纯白而不定的罗网”来反衬,人间的肃杀之气格外浓重。我“在餐厅上”的吃,由于没有寄托,吃得还算自在,除却后半段联想不知趣的叨扰。 怅望千秋,萧条异代。从前的文士如吕纬甫,颓唐之后,可能投身革命,如果不给革死,侥幸成为胜利者,还要过许多关,如批胡风,反右,“文革”。这么善良、敏感的读书人,难保不在某一场或多场运动中吃上苦头。他在落难中,未必不怀念酒楼上那一次,至少有“我”为伴,有低度数的醇香绍酒和热辣辣的油豆腐,可随兴发牢骚。至于我们,一点也不忧国忧民地吃过日本饭,付75元的账单时毫无怨言,还把炸银鱼打包。 门外,雨停,天地清新。不识趣地想起《在酒楼上》的景致:“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老夫子把灰暗慷慨地送给所见的外物,我这点儿快乐却只够自己用,而况街旁的紫荆没有著花,鲜艳的依然是红砖,和飘然过街的两三把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