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也许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但牛根生和郑俊怀,这对曾经同事多年,又打过多年“擂台”的欢喜冤家,在财富面前的态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郑俊怀似乎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而牛根生则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拿了出去。
近期,牛根生发起了“老牛基金会”,牛根生透露,基金会已经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他之外,还有奶协、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但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12月18日下午,本报记者在蒙牛集团总部独家与牛根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交谈。其办公室比较简单,最突出的特点是“牛”多,三个牛造型的工艺品,三张“牛”图片摆在屋内。
作出决定很难
《第一财经日报》:作出建立基金会决定的过程容易吗?
牛根生:2002年年底,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在那个时候,我还静下心来看了一段时间的书,看得最多的是老子的《道德经》。2003年年底,开始运作这件事情。但在作出这个决定后的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生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快乐,一种超越的快乐(说到这时,牛快速松开了领带)。我现在心里也很踏实,不担心别人的恐吓,也没有了别人对我疯狂追求财富的误解,孩子找对象也就真实了。
《第一财经日报》:您的家人是否同意呢?
牛根生:现在我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已经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当2003年年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时,家人、亲戚都很矛盾。在我们家,同意倒是都同意,只是认识深浅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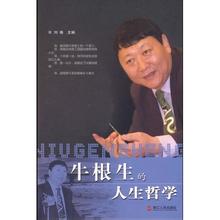
《第一财经日报》:你已经排在富豪榜上了,可听说您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富人,为什么?
牛根生:在创立蒙牛之前,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富人,那时拥有由伊利股票变现得来的100多万元,在内蒙,我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但现在,我却欠着200多万元的外债。至于我拥有的股份,完全只是一个数字,我可能一辈子也花不到,因为在极其敏感的香港股市,我可能一辈子也不敢把股票变现,因为这对企业股价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为什么要让那个数字拴我一辈子?
《第一财经日报》:您希望您的企业家朋友和同事也效仿您吗,他们对您的做法怎么看?
牛根生: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说实话,这样做确实有难度,甚至我的同事和下属都有不同看法。
中层以上都有“接班人”《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这样做对您企业的长久健康运行有什么益处?
牛根生: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钱给大家花,小伙伴就听我的话,办点“坏事”也听我的话。
食品行业本身是高风险行业,像我们这样一个不到7年的企业,必须在竞争方法、措施上有新突破,在管理制度上有新突破。国外该有的我应该有,他没有的,我们也应该有。设立老牛基金会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突破。
对新的董事长、CEO而言,他不仅得到该得的福利,还可以拿到经营上的最高奖。按照基金会章程:在我不再担任董事长后,属于我的不到10%的股份的表决权,将由下任董事长继承行使,他同时还将对基金拥有支配权,以及基金会给予的最大份额的奖励。不仅有话语权,还有分配权,这肯定能够吸引优秀的经营人才,谁能给你这么多?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打造百年蒙牛吗?
牛根生:当然不是,不过我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打造百年蒙牛,仅凭此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您还有其他想法吗?
牛根生:仅靠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它事情如果做了之后,再多做一点就很可能让蒙牛更健康啊。
《第一财经日报》:您成立基金会的最大目的是想让蒙牛健康的发展,那么您在接班人问题上是否有过考虑呢?
牛根生:当然考虑过,我们中层经理以上干部都有接班人,一般来说有两三个,两个接班人在我们的企业中,已经确定且告诉本人,另外一个是不确定的,准备“空降“;董事长的接班人在2002年就已经确定,人选就在我的副总中间。
我没有被外资剥削
《第一财经日报》:有媒体说,在当年上市的时候,您对有些事情并不清楚,结果现在被剥削得很厉害,是吗?
牛根生: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世界上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每一个上市公司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特点,蒙牛是内地第一家在香港红筹股上市的民营企业,很多问题,诸如股权结构都很复杂,要想合法在香港上市,只能请别人,既然是请别人,怎么能不让我得利呢?再说,这些外资有多年历史,之前也同很多国家很多行业的很多公司有很多合作,我们只是其中一个而已,难道股民都是傻子?
《第一财经日报》:您对过去的2004年和2005年的中国乳业有什么看法?
牛根生:2004年是中国乳业比较难受的一年,据网上的消息,伊利折帅、完达山内讧,三鹿蒙冤,三元亏损换帅,我们也曾遭到诽谤,五大外资乳业公司基本退出,这和整个行业残酷竞争是分不开的,现在有的地方奶价竟然不如水价高。我相信,2005年大有希望,因为物极必反,奶业低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反弹。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