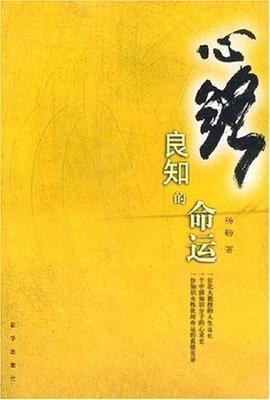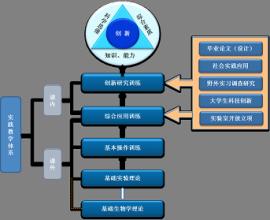今年正好进入不惑之年的高世楫,自认经历非常简单:在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出国的时候出国。1988年,作为第二批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获得者,高世楫被派往英国伦敦的CityUniversity攻读系统管理博士学位,1992年获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Sussex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1995年的圣诞节之夜,在他认为该回国的时候学成回国,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其前身是在中国改革史上注定要留下浓重一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0年来,虽然研究所的“婆婆”换来换去,2004年底高世楫也调到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担任副部长,但这位有着多学科训练背景的学者一直信奉“干中学”的原则,以复杂系统演变的视角思考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真实问题。 与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成长的经历非常简单:改革开放后上初中,高中也只上两年,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每月18元的助学金上完本科后被保送本校研究生,1988年赴英国伦敦CityUniversity留学时所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也是中国政府、英国政府和香港实业家包玉刚三方联合提供的,所以总觉得自己欠国家、欠社会颇多。 1992年我在伦敦参加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一次活动,包玉刚先生的女儿代替年前刚刚过世的父亲参会,其平平淡淡的一句“先父生前是希望各位学成以后能够回去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留学多年,自己回国也认为是自然而然,当然,我也认为那些不回国的人有自己的选择自由。 如果说回国是一种选择,那也是因为我相信,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要做好自己选择去做的事,即投入到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其中体会这种变化给个人带来的喜怒哀乐。我自己一直从事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自认为工作的性质是“知其不可为而说之”。 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是大规模系统有限结构分析方向,在英国读的博士是系统管理,我的学术思想的主线是复杂系统的演化,偏重于系统演变的国际比较研究,最近几年更多地关注监管改革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我认为,制订经济政策的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博弈的过程,每一重大的决策都是许多人从许多方面共同推动后形成的合力的结果,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个人“一言兴邦”的作用。中国目前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艰难时刻,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涉及现存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更需要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证决策能为大众利益服务。从本质上,这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对为13亿人谋福祉的共产党和政府而言,“中国人”到底意味着老百姓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政府有哪些权力和责任,虽然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如何在及时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矛盾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妻子同样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一个大学教书。我的女儿是在妻子博士答辩后回国3个月生的,妻子回国前在英国所享受的包括妊娠后期专门护士定期上门检查的免费保健,与回国后在医院经历的不愉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回国后的第一次逆向文化冲击,其强度丝毫不比初去英国时小。不过,这些年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更多麻烦和忧虑的事情后,当初的烦恼已经显得并不那么难以接受。我一直被朋友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但我对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缓慢的法治建设进程、恶化的自然环境、混乱的是非观念、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失衡的社会心态等等,实际上有着深深的忧虑。
但我仍然坚信,只要我们能够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努力,我们中国人还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我选择从事政策研究的平凡工作,但我希望通过所有人努力干好自己选择的事业,使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占全球20%的人,能够像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过上富裕无忧的生活。我总想我的女儿在20多岁时,能够以生活在强大、富饶、文明的中国而自豪,以持一本中国护照全世界遨游而得到羡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