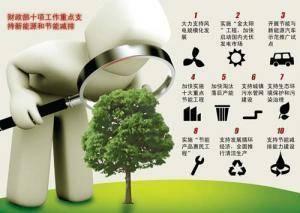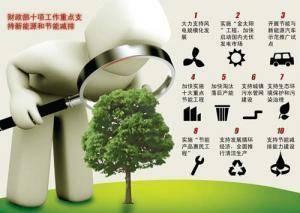系列专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附件一国家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须各自承担一定的减排承诺: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欧盟15国减少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议定书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1%。邹骥:《京都义言书生效:国际气候进程就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2005年2月16日。 非附件一国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人均排放和总排放量激增的阶段,尽管现阶段作出某种明确的量化承诺较为困难,但也应该循序渐进,做出与各减排阶段相适应的努力。这是全球统一碳市场建立的重要条件。

为了降低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成本,同时把非附件一国家也吸引到减排行动中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IET是附件一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AAUs)的交易,各国可以将分配到的AAUs指标根据自身排放情况买入或卖出。JI主要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ERUs)交易,各国通过技术改造和植树造林等项目实现的减排量,超出自己承担的减排限额的部分,可以进行交易。CDM与JI类似,只是交易双方换成了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向非附件一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证减排单位(CERs)。京都三机制把温室气体减排量成功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附件一国家及其企业,可以通过买入减排指标来缓解减排约束,或者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这实际上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中的CDM项目交易,作为一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转移的渠道,也在日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无疑是人类社会迎接全球变暖挑战的重大进展。但这个重大进展的背后,也存在着重大的缺憾,这使它的历史效果大打折扣。 最大的缺憾,是美国的退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大的排放国家,排放总量占全球的1/4,人均排放量20吨/年左右,是英国人均排放量的2倍,中国的4倍和莫桑比克的20多倍。《京都议定书》谈判之际,正值克林顿总统执政后期,在戈尔副总统等的推动下,尽管国会态度消极,美国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京都谈判,不过,克林顿还没来得及将议定书提交给国会审议就已经到任了。随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全盘推翻了前任达成的协议,表面的理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真实的理由则是其最大的支持者能源企业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美国的退出,在京都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几乎要了《京都议定书》半条命。牛仔布什消极抵制之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铁杆盟友也借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其阶段限制。目前,议定书只规定了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2012年之后的目标还悬在半空,“后京都时代”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减排框架将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都还是一个谜。这也是迄今历次气候谈判的核心课题,由于涉及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各国围绕2012年后的博弈也就分外激烈。 气候明星:斯特恩与戈尔 在动员世界舆论关注气候变化方面,尼古拉斯?斯特恩和阿尔?戈尔是两把最嘹亮的号角,真正唤醒了公众的气候意识,并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两位表情严肃、语调平和、讲话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学者型政治人物,在全球气候领域却具有摇滚巨星般的影响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