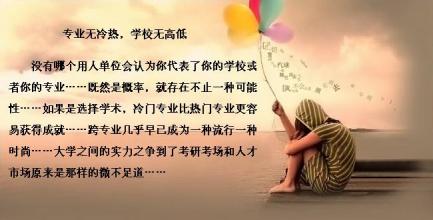近年来,郑小琼先后荣获“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两度获“华语传媒文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一时间,郑小琼这个陌生的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旋风,更在数以亿计的打工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流水线上的“245号”
1980年,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搬罾乡的一个农家。1996年,当她考上四川省南充市卫生学校的时候,瞬间成了家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卫校,毕业后便能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她带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家里人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来到卫校就读。可4年之后,当她从南充卫校毕业时,学校已经不再包分配了,几经周折,郑小琼来到一家乡村卫生所工作了半年。在乡村卫生所的经历,她一直都拒绝回忆,因为那是个梦魇。乡村诊所说到底就是个性病医院,“那些地方太黑了,根本就是在骗人,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我真的看不下去,良心不安啊。”郑小琼说:“上学时我一个月费用要两三百元钱,一年学费要两三千,上学时欠的那么多钱怎么还?更别提回报父母了!”于是,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南下广东打工。2001年3月,郑小琼从四川南充来到广东东莞开始了她充满艰辛和泪水的打工生涯。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更难。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招工单位先让你跑步,还要做仰卧起坐,看看你体力怎么样。人都没有尊严了,反正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如果幸运地被工厂招进去的话,首先便要扣下工人的身份证,又要收押金,也就是先交一两百所谓的制服费;然后是3个月到半年的实习期,在实习期间没日没夜地干活,还要不停地加班,却几乎没有多少工资,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即便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自己能够被工厂录用是一种幸运。”打工多年,见过无数不平事的郑小琼讲起这些经历,心中仍然潜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和无奈。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初到广东,郑小琼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不断转厂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地艰难。“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叫可怕。”但恐慌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饿过一顿是一顿。挨饿之外,暂住证又成了郑小琼的另一个梦魇。“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小孩的打工者,孩子一下子“哇”地一声就吓得哭起来……特别是查房的人手上那个手电筒“刷”地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在打工过程中,郑小琼不止一次被抓过,因为是女孩子,有厂牌,罚完款就走了。而她身边的打工朋友中有的被罚过二百多的、三百多的、四百多的,很多人还被收容过。
工厂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12小时。她在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地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后来,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广东东莞市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一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望她,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她下班,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话。在这个封闭得类似于监狱的环境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五号左右,却只能领到一点少得可怜的薪水。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会争着要加班,为了三个小时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在五金厂,郑小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炉火的光焰与明亮的白昼间/我看自己正像这些铸铁一样/一小点,一小点的,被打磨,被裁剪,慢慢地/变成一块无法言语的零件,工具,器械/变成这无声的,沉默的,黯哑的生活!”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卡号,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郑小琼的卡号是“245号”。这是她在东莞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叫郑小琼,更不会有人知道她在文学上所获得的成绩,即使是知道了也不会有人认同,人们只会说:“哎,245号”。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机台上取下一公斤多的铁块、摆好后用超声波打孔,如此反复。一分钟要从机台上取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再取下,不断地重复这个枯燥乏味的动作达二十几次。她在五金厂上班的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每天上班,都伴随着一种钻心的痛……但这个厂子里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手烂不烂,只管你上不上班,基本上每个工人在上班第一个月手上的皮都被磨掉了,然后再长出一层又厚又粗的老茧……长出老茧之后,便逐渐开始适应这种生活。郑小琼最多一天打过一万三千多个孔,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可以挣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些微薄的收入,在郑小琼看来却是20多年来得到最多的一份工资。而她也一直认为:“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在这个工厂她一待就是4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生活很平静也很清苦。
关于从2001年以来打工的这段经历,后来,她在自己一篇名为《流水线》的文章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虽然时过境迁,语言中却仍然是一种无法掩盖的无奈与辛酸: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
苦难中绽放的娇柔之花
早在2001年夏,郑小琼在东莞一个小镇家具厂做仓库管理员,每天一个人守在一个巨大而凌乱的仓库里,等待其他工友来领胶布、丝攻之类的物品。很多时候,只是她一个人枯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在仓库里,她偷偷地看厂里的杂志,觉得自己也能写出里面的文章,然后写下生命中的第一首诗《荷》:与风痴缠在一起的荷/梦一样美丽/叹息如风/站在夏天的中央星星点点/布满回忆的池塘/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每天/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乡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飘出淡淡的清香……。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郑小琼将这首小诗寄给了当地一家叫《大岭报》的内刊报纸,不久,这首小诗居然发表了,这满足了她小小的好奇心,从此写诗成了郑小琼生活的一种寄托。如果被人发现她上班读书写字,后果就是罚钱。于是她悄悄地把诗写在随身带的小纸片上,下班后再整理到一起。稍作修改后她会偷偷地往外投稿,之后各地的用稿通知和诗人朋友的信不断涌来,令人气愤的是工厂里转交过来的信竟然要收工人们的钱,对此,郑小琼一脸的愤怒与无奈。
“她们丢失了姓名,籍贯,年龄,她们在这里/只是一个数字或者流水线上某个工序的名称/她们就这样,在别人叫唤中磨亮着自己的青春”。郑小琼在一首名为《打工妹》的诗篇中写下了上述诗句。找不到工作时挨饿,甚至有一次被工厂拖欠4个月工资;写成的诗稿在搬迁中丢失……在东莞打工过程中的种种不幸遭遇使郑小琼痛苦和悲愤,却也成为她写诗的动力。写诗是她唯一能感到快乐和自由的时刻,她成天沉浸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与灵魂对话。
有一次,郑小琼的一个朋友因无暂住证被送进了收容所,几个老乡四处凑钱才将其赎了出来。这事让郑小琼感慨万千,并写下诗歌《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读着陷阱,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两年来,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落下一滴泪/一声咒骂,一句憋在心间的呐喊/我听见的打工,一个衣冠不整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和匆匆夜色,行走,或者/像我的兄长描写的那样/‘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我见到的打工,是一个错别字……”
2001年,郑小琼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井冈的竹》在《东莞日报》副刊发表。同年,郑小琼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东莞日报》征文比赛三等奖。这一次的获奖,让东莞的诗坛记住了“郑小琼”这个年轻的名字。此后,她一发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花城》、《星星诗刊》、《诗潮》、《诗歌月刊》、《山花》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
几年间,郑小琼写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并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清华说:“我读到了一位叫做郑小琼的年轻人的大量书写厂区劳工和个人生活的诗,我得说,它们非常令人感动。我以几乎最大的篇幅选入了她的5首作品。这位打工诗人的锐利,会让多少自认为专业和富有技艺的诗人无地自容啊。”他评价郑小琼的《完整的黑暗》:“三条鱼驮着黎明、诗歌、屈原奔跑/对称的雪沿着长安的酒融进了李白的骨头/列队前进的唐三彩、飞天、兵马俑/化着尘土的人手持红色的经幡演讲/达摩圆寂,天生四象,六合断臂/死亡是另一种醒来/时间的鸟只抖落了皇帝的羽毛……”。“这是何等境界和气势,整首诗一气呵成,气势贯通,绝无叠加拼凑的痕迹。称得上是对一个时代的整体俯瞰,非常富有概括力、悲剧性、精神深度与抒情力量,如果再考虑到她的那些随意铺排的,如悲伤的夜曲一样的抒情短章,郑小琼可以称得上是一颗瞬间升起的真正的文学‘新星’。来自底层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了她厚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叙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2005年12月,郑小琼巨大的照片和13首诗歌作品在第12期《诗刊》发表后,她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打工诗人身份,在当代诗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引起了全国诗歌界对打工文学的大聚焦,郑小琼成了中国当代“80后”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直至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界和网络上对打工文学的讨论和关注还在继续。
两年之后,即2007年7月,郑小琼以散文《铁·塑料厂》站在当年《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的颁奖台上,提到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创作动机,她说:“听说珠江三角洲有4万个以上的断指,我经常想,如果把他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可这条线仍然在不断快速地增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她说,自己的指甲也被机器轧掉过,所以深有体会,自己的作品也多是关注工厂和打工群体的。她的发言数次被掌声打断。这一次,她感动了所有人。人民文学奖评委对她的评价是:“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为我们现代工业制度进行反思提供了个人例证。”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