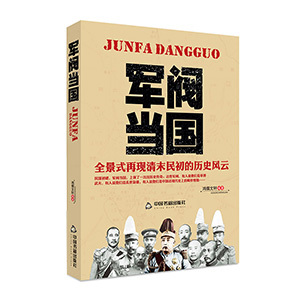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一本书:《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荐书的三天前(4月17日),李鸿章已经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场急风暴雨,开始迅速涤荡中国知识界。
邓华熙所推荐的这本《盛世危言》,俨然成为那只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将该书印制2000部,发给朝中的高干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牙牙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婴儿,名叫毛泽东。
这本畅销书的作者郑观应,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兼思想家。这一年他53岁,正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经理(总办)。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叔,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当时,他的另一香山同乡、比郑大4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中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应”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总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的关系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经营的私人生意。
盛年退隐著书立说
但此时,“千手观音”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斗。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音”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台邵友镰奉命查办。结果是,台面上虽查无实据,却发现郑融进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最后还是郑自掏了2万两银子补账。
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难咽被窃之气,便将担保人郑观应扣起来一起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这时,郑观应还花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修道炼丹。在修道炼丹之外,郑还大娶侍妾,以至于晚年郑观应要教育儿子:“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他在后来的遗嘱中,也特别强调“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可见当年的他,对纵情声色是很投入的。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还担任了汉阳铁厂总经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复出之后,“千手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里,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直到去世。
矛盾重重人格分裂
“千手观音”终其一生,似乎都一直显示着“人格”的分裂: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他总是热衷于开创新业,也同样热衷于在遭遇困难时抽身离去;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经商的本事要差得多;他高调反腐败,提倡有德行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还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声色。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后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他被塑造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迷信者。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