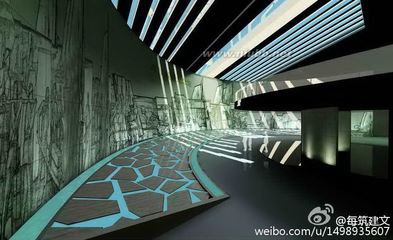对于于是之来说,读书,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于是之常常在强调,演员读书一定要学以致用,为了工作而学。每演一个新角色,都要涉足于一个新的生活知识领域,而认识这个新领域,除了到现实的生活里去体会外,就是要读书。一个演员只要是创作不止,就应当读书不止。
曾经有一位朋友对于是之说过:“我祝你健康,因为除了健康之外,你什么都不缺。”于是之却真诚地回答:“除了健康,我还缺文化。”于是之非常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并常常觉得自己在他们的面前自惭形秽。他曾经写了这样一些讲给青年演员的话:“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把无知当做有趣者。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能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竟是一个杂家。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这样,便能促使我不断地有些长进。”
无需讳言,于是之的艺术修养是相当深厚宽广的,也是相当坚固的。他十分信奉俄国大导演梅耶荷德的观点:“艺术的美妙,就在于变化,就在于你时时觉得自己还只是个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多少次看到于是之在读书,无论是在家里、排练场、演出后台、汽车上、火车上。我记得,那部托尔斯泰写的厚厚的《战争与和平》,他就是在《女店员》巡回演出的后台,利用空闲时间看完的。不论后台里有多么热闹,有多么嘈杂,他都能“当众孤独”地坐在化妆桌子旁边,静静地读自己的书。他的读书习惯,已经到了一种“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刚刚从事专业编剧工作的时候,于是之告诉我最好每个星期至少读一本世界各国的、中外古今的经典话剧剧本,而且最好是认真地读,并写下笔记。如果说,我在戏剧文学上还有一点点积累的话,和那几年(每年读五十二部)坚持每周精读一个剧本是分不开的。在近些年里,是之不止一次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们终于在议论‘非学者化’的不足了,我是极赞成的。以我的教训为例,没有学问的演员大约是不易取得大成就的。我们必须成为自己所属的专业的学者。我要大声疾呼:要提高多方面的修养,包括文学的、美术的以及所有的。”
他也曾公开表示过:“交响乐、建筑和书法,大都是不具象、无情节的艺术品,但都有美:形色的美、节奏的美、韵律的美。书法里,有的秀逸,有的遒劲,有的古拙,但都有自己的美。由此我想到,演员的创造更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关于诗论、画论,我曾偷闲读了一点点,觉得好。也曾立志读下去,但终于不可能。读到冷僻一点的辞句,老实说我不懂。外国书看不懂,还多少可以原谅;祖国的书,自己‘母亲的语言’,竟然也读不明白,就觉得万分愧疚了。但也只得作罢,不掩卷而长叹又当如何呢!”
于是之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愿意学习,是因为总觉得有一个无形的神或鬼压迫着自己,催促着自己:“为什么一些普通的常识你竟白痴一样的不懂?许多名著你为什么不读?”
记得不久以前,曾经听到一位青年话剧演员——还是一位有了一些名气的话剧演员——当众大言不惭地说:“演员只要能把台词背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他哪里懂得,一个演员只要一上舞台表演,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修养、对于角色的创造态度和创造程度,就会掩盖不住地显露出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