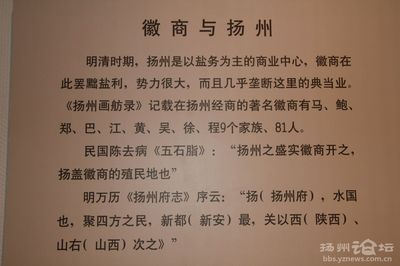浙江虽为鱼米之乡,但浙人重商轻农的思想却由来已久,这倒不完全归咎于浙江出杭嘉湖平原一带,多数地区为山地丘陵,土地耕种面积小,而人口众多的原因。就文化而言,中国古来就把商人放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士、农、工、商。既然做个商人不是有钱就能改变社会地位,更多的人便把追求入仕做官当作一个门径。
读书人纷而达至入仕的独木桥,光耀门楣成了流传千古的传家故事。读书人自有朝以来,不屑以经商成为定式。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虽然就其经义而言,我们能够窥看到先哲经世济国的宏伟社会报负,但真正让浙江读书人解放思想、投笔从商,仍是浙东学派的思想流布乡间之后。
浙江自唐宋以降,便成为朝廷的米粮仓和国库税银的重要来源地。尤其在明清,浙江工商发达,高出其左右。然而浙江也一度成为全国最为落后的省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竟然出现过其他省份支援“浙江懒汉”这样的事情。
浙江的快速发展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
现在我们说道一个人成不成才在于他有没有思想,一个企业发不发展在于它有没有好的机制,一个社会发不发达在于它有没有好的体制。一言而蔽之,都在于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解放,解放了思想,才能最大程度的解放生产力。浙江人懒不懒,不是用一两句话可以说的。浙江人确实有一段无法养活自己的凄惶日子,这是为世人落下话柄的谈资。
然而当下的浙江人不仅务实吃苦,还敢为天下先,一跃成为国内最为富裕的人群。与浙东学派的思潮从很大程度上是分不开的。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的思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浙江学人一贯对商业的认知。这一点在潘起造先生的《明清浙东学派对经世致用传统的传承》文中有了明确的说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他指出:在经济观念上,浙东学派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同时,他对那些为奢侈迷信服务的商业又主张加以禁止,认为“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娼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黄宗羲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所谓“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论上说明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从而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观念上,浙东学派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强调国家应以“保民”、“养民”为最高职责。在为何富民和怎样富民的问题上,儒家主张:一是要以农为本,致富的办法是“强本”、“务本”;二是在富民的目的上把强国放在第一位,认为富民是为了强国;三是在富民的原则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论。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首先,他们所重视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认定“商贾”与“力田”一样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们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夫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富国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们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黄宗羲一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不能“夺富民之田”,主张对富民也进行授田,“听富民之所占”,反对均富。这种富民观念显然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