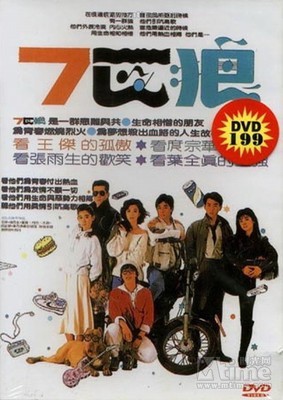清晨,坐友人的车出游。冬雨初停,举目处皆萧瑟。友人夫妇站在树下,向我招手,我向他们停在街旁的轿车走去。就在这一刻,风,挟着西伯利亚寒流,撼天动地而来,遭一排大厦拦截,十分地不顺气,遂改俯冲为与河涌的绿水平行的角度,从背后扫过来。我打一个寒战,裹紧晴雨两用夹克。
奇迹在瞬间呈现。眼前重重叠叠的洋紫荆树,簌簌地下起绛红色豪雨。最近,这种树趁着天气暖和,开得最为恣肆。雾霾连天,目光所及,无不朦胧,浑沌。唯独紫荆花和雾气对着干,在十字街口,以比交通灯的红色醒目得多,霸道得多的群体气派,向天空示威。而这一带,除了落雨衫,行道树以紫荆居多。风云际会,花落成线,成片,成团,路旁停着的车子,一眨眼变为花山。我的朋友夫妇一边挥手遮挡一边笑呵呵地走近,头上,肩上,鞋子上,无处不是花。我差点大叫一声:“先别动,让我拍一张照片!”可惜风声太大,他们听不到。
“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景致,在春天的桃林,不难领略。可是,桃树都低矮,雨所占的空间有限。论气势,当然是比桃树高出一倍的紫荆树领先。按照这逻辑,高可参天的木棉树,下起花雨来,该压倒紫荆,而况花瓣猩红,从九天泻下“血的瀑布”,视觉效果更加强烈。然而木棉花太稀疏,十棵树的花也比不过一棵高产的紫荆。看来,还是紫荆花雨居首,既常见,场面又大,这里的居民有福了。
“花雨”一词,中学生时代已在书中读到,但形成美学的憧憬在“文革”年代。第一次造访语文老师的家。他家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圆柱形烟罐,楠竹做的,从前该是他那开制作神龛的小店的老爸,拿来盛“三炮台”一类香烟的,如今家道中落,罐子里面只是呛人的廉价生切烟丝。罐子周身发出润泽的褐黄色,可见年代久远。罐上的图画笔画简约,一个亭子,亭内两个雅士,一坐着操琴,另一背手看槛外,似在吟哦。画下有阴文:“一亷花雨,半榻茶烟”,颇地道的瘦金体。我把玩罐子之际,他家楼下的大街,传来杀气腾腾的林彪语录歌:“上战场,枪一响,完蛋就完蛋!”拨开窗帘向下看,红旗遮天,人如潮涌,一队“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着,狼狈而行。我和被我视为文学偶像的语文老师相视苦笑。其实,我们也是这般发热昏的红卫兵,刚才还和他一起写了和“保皇派”对骂的大字报。那世道,岂能容忍“花雨”之类的诗情?
按说,当完“四人帮”的炮灰以后,在乡村,“一亷花雨,半榻茶烟”的境界,从低层次而言,不难进入了,不就是下雨天,无法出勤赚“大寨式”工分,姑且猫在青砖老屋,半躺在冰凉的酸枝木炕床上,和同病相怜的诗友,喝一杯最便宜的“清明茶”吗?雨在遮盖天井的薄铁皮上敲着,有如马群奔踏。“花雨”在门外三尺处,一株歪脖子苦楝树,开着白色花,并不茂盛,风来,虚应故事地落下数十朵,粘在女墙上,一似饥寒交迫的无告者。
好在,今天,多情的寒冬,送来远远大于“一帘”的花雨。对面的如果是穿淡雅的旗袍的江南丽人,纤纤玉手拈花向我嫣然一笑,该是何等的娇柔!好在,友人夫妻虽年近花甲,却一点也不煞风景,相反,红色的女式风衣和黑色的男大衣,淡定的步履,给连天的雨丝注入沧桑的景深。此刻,若仅仅要“一帘”,也轻而易举─到紫荆树旁边的茶庄去,拣一个靠窗的座位,喝一杯功夫茶。迷尔的杯子里,茶先苦涩后甘凉。且回味1967年第一次看到的瘦金体,帘外红雨洋洋洒洒。大半辈子如烟云消逝,如今却无与我相对的故人。
远游归来,已是黄昏,回家时从紫荆林中穿过,那些向北方敞开的角落,无不绛红成堆,那就是花雨之后的“积水”。想起苏曼殊诗“落红深一尺,不用带蒲团。”恨自己不是僧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