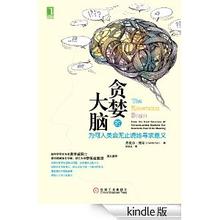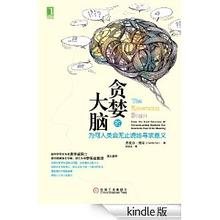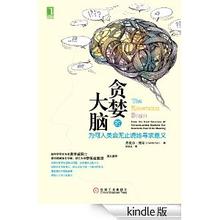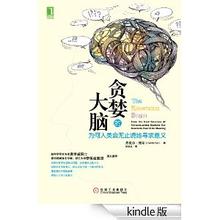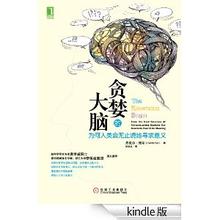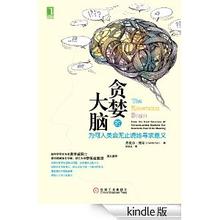
基因突变是向DNA编码中注入新“想法”的最明显的途径。尽管DNA分子很有活力,但并非完美,偶尔也会出错。以细菌为例,每1 000万个字母会出现一个错误,而细菌有10万个字母进行DNA编码,也就是说100个细菌包含的字母中只有1个字母发生1个错误。有些错误不会导致生物性状的变化,因为这些错误只是另一种编码形式。而另外一些错误会改变蛋白质的构成,从而严重影响细胞的功能。基因突变带来进步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大可能产生有利于生存繁衍的更好的“想法”。
对所有有机体来说,为了获取更多的新“想法”来应付动荡的环境,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控制基因突变的数量。一些物种确实利用了这一办法,比如细菌在形势严峻、生存压力加大的时候,会增加基因突变数量。酵母菌面对生存压力的反应不是基因突变,而是改变整个染色体的结构,这种做法能产生同样效果。
有趣的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灵长类动物身上。社会地位较低的灵长类动物比地位高的同类更喜欢标新立异—希望通过这些举动获取高一级的地位。人类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战争总是会带来技术的飞跃。
动物的基因突变率虽然和细菌相似,但是存在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动物基因的形体要比细菌大很多,结构也更为复杂,动物进行自我复制的速度比细菌慢50万倍,这就导致动物基因的创造力远远不如细菌基因。很多动物应对变化的能力非常差。6 500万年前,陨落到地球上的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尤其是对恐龙而言。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动物不能适应这颗行星带来的气候变化,75%的动物就是因此消亡的。尽管不可能收集到因这一事件而死亡的细菌数量,但是细菌的死亡比例很有可能很小。由于细菌能够很快适应这颗小行星坠落带来的可怕环境,进化选择了这些生存在大多数物种体内的新型的细菌,而这种选择破坏了进化过程。
为了弥补复制速度缓慢带来的严重不足,动物开始进行性繁殖。从很多方面来看,性繁殖是一种新策略。尽管细菌主要通过简单的分裂方式繁殖,在繁殖过程中保存每个基因,但是细菌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性繁殖:通过与另外一个细菌(甚至是其他种类的细菌)结合,替换对方的基因编码片段。但对动物来说,性繁殖是一种必须,而不是例外。
从“自私的基因”的观点看,沉溺于性繁殖而不是进行简单的自我复制会带来一些小祸患,因为只有一半动物基因的特性传给下一代。但是性繁殖会提高基因创造力,这证明性繁殖的方式是有价值的。动物两性的基因混合产生新的基因信息,能提高后代应付危险的能力。这种补偿复制速度慢的方式极为有效,所以大部分动物都进行性繁殖。
充分利用性繁殖的一种动物是地位较低的线虫(nematode worm)。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线虫中的一种类型,成为基因研究的模式生物。秀丽隐杆线虫结构简单,发育后代的速度很快(约为4天),繁殖方式为有性繁殖。这种线虫可以自由选择生育后代的方式—通过自体受精或者与其他线虫交配。
从信息处理角度看,如果线虫生活的环境很安全,有充足的食物,那么不妨采用自体受精的方式,因为它的有关生存的基因信息准确无误。但如果线虫生活在有致命危险的环境中,它的下一代的DNA就要做重大调整,而经性繁殖产生的下一代可能具有更好的基因来应付恶劣的环境。秀丽隐杆线虫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繁殖的。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遇到像细菌感染这样的威胁时,秀丽隐杆线虫很可能放弃自体受精,而与其他线虫交配繁殖,使其家族世系有可能存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其他线虫交配产生多样化的基因,虽然会造成混乱,但还是有利的。相反,那些无视危险进行自体受精产生的后代,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不出几代就会马上消亡。
另一个保持基因创造力的方式是死亡。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机构让那些脾气暴躁的老教授到一定年龄退休是明智之举,这使得顽固过时的理论和思维习惯不能长久地影响学术圈,也使年轻的、富于创新思想的科学家有机会展现才华。同样,在自然界,死亡很可能使生物体避免积累过时的信息。有机体在逐渐消亡,这是事实。生物成功生育后代后突然出现的致命的基因疾病不是进化关注的重点,这也是事实。但这些并非事实的全部。
在某些情况下,死亡也会陷入困境,似乎并不那么确定。比如,生活在寒冷荒凉的南极地区的一些细菌,生命处于停滞的状态,但还活着,如果有必要还可以这种状态活上几十万年。另外,所有被测试过的有机体—从酵母菌、虫子到人类,仅仅通过少吃点,至少能增长1/3的寿命。因此,这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机制,使生命体坚持得久一些,直到有足够的食物,而且环境变得适合生育下一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死亡像是事前设计好的,具有灵活机动的特性,而且很可能有充分的理由。
如果没有自然死亡,一个物种的基因创造力会受到过时的思想的损害,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损害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年老的一代不消亡,有着创新思想的后代很难得到发展,因为家庭内部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代,那么优秀的思想会变得越来越少,而这一物种对外界变化的反应也会越来越迟缓。一旦出现危机(年老的生物是无法解决这些危机的),这个物种应对危机的能力会非常差。而如果正常更新换代,情况会好很多。
这也是我们通常不会全部记得所经历的事情的原因。牢记那些不断增多的不相关信息,会严重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使我们患上精神疾病。有着惊人记忆力的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ashevski)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所罗门生于1886年,在一个俄罗斯籍犹太人的小团体中长大,近30岁时成为一名记者。
就在他做记者后不久,人们才发现他具有超人的记忆力。一天,编辑与往常一样在早上开会,给记者分派采访任务。每个人都忙着做笔记,除了舍雷舍夫斯基。他甚至连笔和纸都没带。编辑认为舍雷舍夫斯基太懒了,对他很不满,让他解释为什么不做笔记。舍雷舍夫斯基说他根本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听到的每一句话,而且向来都如此。编辑不相信,让他马上证明。舍雷舍夫斯基照他说的做了,一字不差地复述了编辑在当天早上说过的话。
实际上,舍雷舍夫斯基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其他人会和他不一样?为什么其他人会马上忘记这些重要的事情呢?这意味着什么?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舍雷舍夫斯基异于常人了。舍雷舍夫斯基被送到俄罗斯著名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那里,亚历山大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舍雷舍夫斯基的记忆力。
舍雷舍夫斯基的记忆力确实惊人,他似乎能很轻松地记住所有事情。举一个例子,有人对着他用意大利语大声朗读但丁《神曲》里的段落,而他根本不懂意大利语。15年以后,他能够准确地复述这些诗句,连重音和发音都与当初他听到的一模一样。
拥有天赋的神奇记忆力也要付出代价,这种记忆力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影响不严重,有些却很严重。其中一个缺陷是偶尔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也就是说,舍雷舍夫斯基不能理解所记住的信息的意义、结构及模式。他能记住一长串的数字,却完全不知道简单的数字排列结构,例如他就不明白1、2、3、4是递增数列。
上述这些思维方面的怪现象与超强记忆力带来的情感困扰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由于舍雷舍夫斯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他经常会把现实当作幻想。想象力严重影响了他的现实生活,他做一件事要费很大的劲,比如看小说这样寻常的事情对他来说却很吃力—小说中的每个字都引起他的想象,形成很多画面,让他分心。出于同样的原因,舍雷舍夫斯基努力地克服过去的经历给他带来的重压,他甚至对一岁之前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他极力想抹去过去沉重的记忆,因为那些记忆中包含了早期的一些令人紧张的情绪,如恐惧和婴儿时期的哭泣。
舍雷舍夫斯基的例子说明,有时候旧有信息的消亡反而能让人更成功。一个人适当地忘掉一些过去的事情,有助于准确、有条理地思考当下的事情。同样道理,老一代生命体的死亡能使一个家族或物种有更强的能力应对变化的环境。
进化的动力就是繁衍后代,生存居次要地位。死亡作为一种进化手段,展示了繁衍与生存之间的矛盾:为了使基因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最新的相关信息,有利于繁衍后代,有机体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生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