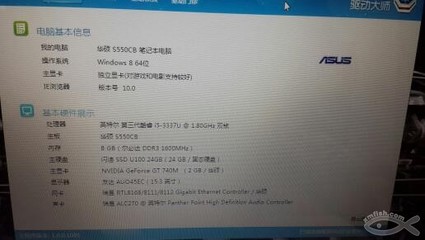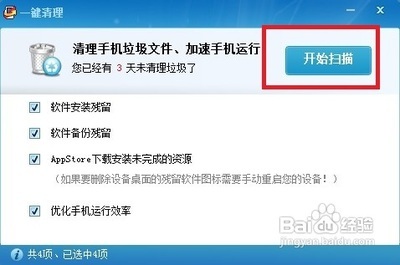曾被齐声叫好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没料到IPO刚一开闸就一地鸡毛。1月23日,8只新股恢复交易之后再度大涨触及二次临停限制,遭遇二次临停。
当前,新股“三高”不但没有被抑制,反而衍生出了老股疯狂套现的新问题,一度迫使证监会胁迫、叫停了奥赛康的新股发行,随后用“打补丁”的方式来恢复证监会行政干预IPO的权力,并重新捡起市盈率评判的标尺,接着五家公司因发行市盈率过高而暂缓上市。更为奇葩的是有些公司为了尽快上市和迎合证监会的“价值判断”,索性将90%以上的高报价剔除(众信旅游剔除了96.33%的高报价),竟让最低报价者收获新股,这俨然违背买卖和交易的基本原则。如此不堪和荒唐的新股发行彻底暴露发行制度改革是失败的,所谓的市场化其实是“伪市场化”,从证监会“愤怒”的表现来看,行政干预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变本加厉。
对于一个将96%以上报价视为非理性报价的市场,显然不是个别机构的问题和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借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著名论断:“凡是大面积出现的问题,一般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凡是长周期、反复出现的问题,一定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如果新股发行再不从体制机制上反思和深度市场化改革,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即使监管部门通过行政胁迫的方式让发行价暂时下来了,但缺乏市场定价机制的市场将会通过新股上市首日和二级市场迅速回补“非理性空间”,而且迫使证监会永远要伸手行政干预,一旦手缩回去,各种潜在的推动力量就迅速反弹,新股“三高”仍然是潜在隐患。
批评发行制度改革失败并非反对市场化改革,反而是希望更加市场化和系统化的改革,如果一个市场只喊“市场化”的口号,而权力发审的行政审批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何谈市场化、注册制改革?
况且,这一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但没有斩断IPO过程中的各个利益链条,反而加大了主承销商自主配售的权力,让主承销商自主选择配售对象,自然报价越高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机构才能成为配售对象,低报价获得配售正常吗?再比如这次发行制度改革对主承销商“直投+保荐”没有任何提及,主承销商手里拿着大量原始股,他们保荐承销能客观、公允地定价吗?还有新股发行意见稿要求“网下配售将不低于40%的份额定向配售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这无疑变相地告诉全世界新股依然是无风险收益,新股申购的能不多吗?这样一来,主承销商手中的筹码越多,越有拉高发行价和上市价的冲动,“直投+保荐”模式不除,主承销商做高发行价和抬高上市价的冲动永远存在,新股“三高”仍难以从根本上剔除。
当务之急,证监会需要重新反思新股发行制度,应该想方设法地“去行政化”和营造法制化、市场化的“注册制”条件,不要再等待和过渡了,目前的这种过渡对注册制没有任何帮助,无非是制造了更多圈钱的IPO。如果投资者没有有效的维权机制,没有集体诉讼制度,市场如果没有严格、公开的注册筛选程序和法律约束,只突出投资者和中介机构承担责任,无异于摆脱发审委的责任而放大投资者和市场的责任,如果是在市场化的注册机制下由市场和投资者自主选择上市公司,如果投资者能够依法诉讼维权和能获得民事赔偿,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天经地义,但在目前核准制下,行政部门决定上市公司供给,这本来就不是市场化的行为。如果证监会真的有心实行注册制,不妨先将目前证监会发行部的审核人员和发审委员部分划归至交易所,先简单从形式上做出区分,告别裁判员与运动员一身兼的角色,监管机构重点负责客观的监督之职,让交易所行使把关之责,只有这样才能算是注册制的雏形。
同时,需要尽快完善退市制度和投资者司法维权的机制,如果一个市场只进不出,投资者诉讼无门,拟上市公司IPO冲关的违规成本很低,发行人自然无法理性选择上市,也不利于注册制的推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