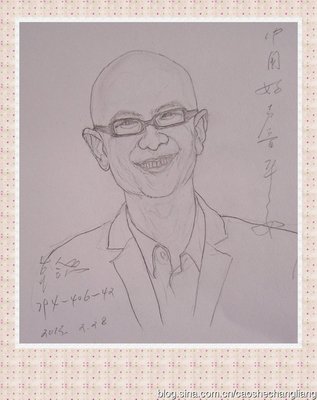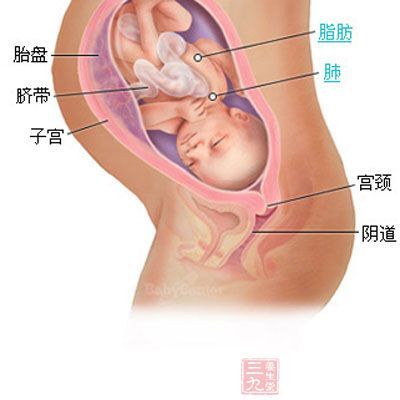7月4号傍晚5点多,京剧演员关栋天从梅陇镇伊士丹走向美琪大戏院。路上,有黄牛(票贩子)在他身侧低语:“周立波(的)大哥,周立波(的)大哥。”
尽管父亲在武汉病重,关栋天在7月档期里仍然每场必到。7点半演出铃一响,他精神抖搂地走向大灯照耀的舞台,以一派高亮嗓音,“沦为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的报幕员”。
上海滩出了一个周立波。据说,有些办公室天天在放他的碟片,有些领导干部也在悄悄模仿他。“哪意思啊侬”、“奈伊做特”,成为切口或暗语。
上海文广演艺中心总裁吴孝明告诉记者,《笑侃三十年》连演31场,场场爆满;《笑侃大上海》45场票,5月20号一天售罄;6月预售12场票,一天售罄,这是舞台艺术边缘化之后,很久没出现的景观了。
“而且今年是金融危机,大家肯掏380、280、180、100块来看周立波。”吴孝明站在后台,底下是乌泱泱1300位观众。当天的黄牛票,380元炒到800元。
幕后
此前贵宾室里,上演幕后戏。
5点20分,司机送周立波及助理到奉贤路。助理有个港派小弟的名字:家豪(音)。家豪从后备箱拎出一套包好的演出服,白衬衫、裤缝笔挺、名牌墨镜的周立波从后座下来,一同进了贵宾室边门。此时他的头势(头路),已然煞清,好几两摩丝喷在上面,定了型。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一个平常演出前的2小时又10分,很难体会什么叫成名,或走红。周立波认真地接受了我的第二次采访,只听得照相机咔嚓在响;待一回头,一架摄像机不知何时已经架好,接着,另一台进来了,编导是从北京飞来的,包里揣着一百多页打印好的已有报道。
一家三口进来了,是熟人。“大师大师。”熟人热情握手,接着引荐中学生模样的儿子,后者见到偶像,惟有羞涩。一家人来看《笑侃大上海》,先来后台瞻仰“下蛋的鸡”。
又一家三口进来了,有人引荐说,这是某市招商局局长,特地赶来。“某市这几年发展不错!”接过名片,周立波道。
关栋天安静地对付完面前一盒快餐,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轮到周立波吃盒饭,热闹来了——这二位在镜头前吃盒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连三天全是咸肉,一点创意没有。”周立波嗔道。忽而挟起一块,挑得高高的:“这块咸肉我很熟的!我本来对咸肉很尊重的!”忽而又怨几只细虾“断七”(人死后做头七,这里意指虾死了很久)。一旁摄像机,赶紧捉下生动活泼。不过,他很懂得爱惜羽毛,“我抽烟时不要拍。”包括应酬,他每天2-3包烟,穿插雪茄。
接着化妆。一只小包,七八样家什,周立波不用化妆师,在脸上打层粉底,再用大刷子于两颊、眼睑、额头扫出几片红,两三分钟,完事。

接着换装。衬衣、西装、背带西裤、闪着金光的背带扣,再戴上支架藏在后颈的话筒……这一套度身定制的名牌,大约5万元——“要用就用最好的”,上海人素来如此。当年在上海滩碰到关节、呆不下去、只身往武汉时,周立波带上火车的,是几大箱衣服——上海人爱穿,素来如此。
其间,见缝插针接受一家电视台由“上海这座城市”起头的采访,周立波侃侃而谈“海纳百川……”然而,当他草稿也不打地讲到城隍庙、阳春面、蟮糊面、王家沙的点心,讲到小时候挖黄沙、打弹子、跳格子、放鹞子,一干上海人都笑了——面前这位,多么标准的“一只上海男人”(周氏节目用语)呵。
其间,见缝插针喷了10分钟的药。助理家豪抱来一台仪器,咕噜咕噜冒汽,嗓子有点发炎的周立波嘴巴被套上,有片刻的安静……不,他又趁换口气的当儿宣布:“周立波在‘吸毒’。”
沙发上,结交20多年、“亦父亦兄”的关栋天纹丝不动,闭目,养神。其实刚才,当咸肉成为道具时,“周立波的大哥”笑着说了一句:“因为太熟,不敢下筷子了。”
台前
石库门布景。《笑侃大上海》第N场。灯光在舞台打出斑驳的绿影。音乐柔声。
舞台上只有一个架子,一只夹子,六七张打印着2号字的A3纸摊开,一支笔,一块白色小手巾。周立波用笔勾掉已讲的段子,用手巾擦汗。
关栋天向观众交待:“这只赤佬人来疯,大家掌声越热烈,他的表演越精彩。”与此呼应的是,周立波在台上做现场调查:“已经看过(盗版)碟片的请举手。”乌泱泱一片。可见潮流、热点来时,也蛮疯。好在,如周立波搞笑所言,这是一场“台上与台下共同完成的鲜加加(鲜格格的变音,约指快乐到轻浮)运动”。
上海音乐学院在读研究生沈灏坐在键盘后面,负责在周立波甩包袱时添加合适的音效。譬如,当周立波向观众申请“喝口水”后,配上抽水马桶的冲水声。精心设计,点到为止,起到提示、烘托笑点的作用。
沈灏跟着周立波的言语动作,也笑——他每晚都要听一遍的。
“您一起演了这么多场,还笑得出吗?”记者问关栋天。
“笑得出。这家伙常有即兴发挥。”关栋天说。
这一场的演出没有模仿领导人的段子。虽然在台下,周立波不经意就冒出某些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的声音。事实上,他学上海本地人“妹妹,给这边上碗咖啡”、学周柏春老师的豆沙喉、学小沈阳“这是为什么呢”,学苏州人相骂“杀煞倷只千刀”,都像极——十年大可堂的基本功,不是白练。
这一场,调侃对象增加了上海倒掉的房子:“房产商也不要太过悲伤,你们的房子还能卖,当平房卖;如果业主已经入住了,也没有什么,不过睡下去的时候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在墙上。”
增加了对迈克尔·杰克逊的另类怀念:“他是黑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后来变成白人我也喜欢他,现在变成死人了,我还是喜欢他。他那只鼻子里,多少违章建筑啊。”
挖苦了深圳市长许宗衡:“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可怜人民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以后要敢于讲:我是人民的老子。因为老子不问儿子要钱的。”计数器显示,强笑声一次。
据周立波说,现场计数器告诉他:一场120分钟,笑声680-700次,平均每15秒观众笑一次。“我要稍加控制,为观众健康考虑。”早些时候,也有观众笑得很恶心、笑到吐出来的。
与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一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与时事新闻的关联度非常强。区别在于:前者是三个人聊家常式地讲,后者是一个人搞笑编排,戏味更浓,可能达到的浓度更高,表演者也更恣意(周立波语)。
当然,周立波以上海男人的“头势清爽”(思路清晰)、“有轻头”(有分寸)有言在先:“先拿肩胛(责任)写清爽,以上所有观点,仅代表周立波扮演的周立波的观点,与周立波本人无关;今晚大家笑过算过,米索拉索。”他狡黠的小舌头,舔了舔左嘴角.
周立波的父亲是位技巧教练,能够胜任叠罗汉最下面的“底座”。母亲,在他的节目中常以左右手拖鞋各一、上中下三路出击“请他吃生活”(揍他)的造型出现,现实生活中每天必跟儿子通个电话,“听听声音也好”。至于姐姐,“相当于半个妈”,“跟我妈一样,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1967年出生的周立波自述家境尚好,如当时上海人家多用马桶,而他出生时家里就用抽水马桶了。“家里人很早就知道我是个天才。”一个调皮捣蛋孩子干的一些坏事,如今回想起来简直是精品,尤其配上经过10年专业训练的动作与表情。好比如何喂隔壁好婆(阿婆)的鸡吞下29根橡皮筋,看着它翻白眼、扑腾,直到不动了;好比如何腰插3条年糕离家出走,沿着铁轨走,“去北京见毛主席”。那些记忆,每个人多少都有,但听周立波讲,不知怎么就那般神形兼备。讲着讲着,他偶尔也会豁边,分不清到底是滑稽戏,还是人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电台有档晚间6点的曲艺节目“说说唱唱”,伴着许多家庭一道度过晚饭时间。姚慕双、周柏春、王双庆、翁双杰、吴双艺、童双春、筱生咪、孙敏……上海滑稽界这些前辈,在那个破碎了又拼拢来的年代里,让老百姓大规模练习一个动作,笑。日子过得太苦或太甜,笑都是不容易的。
14岁那年,周立波跟姐姐被父亲领着,一同去襄阳南路大可堂报考上海滑稽剧团。那一年,共有2800多位考生,其中有15岁的王志文。姐姐第一轮就被筛了,周立波进到第三轮。面试,考官之一是严顺开,考题大约是描述一下你们家新添的大彩电。
“黑白分明。”周立波说,当年词汇实在有限。
“彩色电视机怎么是黑白分明呢?”考官问。
“哦,那天刚好在放黑白片。”14岁周立波的反应。
严顺开当场拍板,“回家等通知吧,不用再考了。”考试一共进行6轮,最后取了16人。王志文没被录取,走上一条更适合他的路。
17、18岁,周立波在太仓路姚家住了两年。并非坊间传说的姚慕双老师厚爱传艺——周立波说,姚老师当时的形象是长久地嵌在阳台太师椅上,一动不动,顶多招呼一句,“来啦,小波。”
周立波深得姚家阿婆欢心——他从小就讨人欢喜,只要他想——并与姚慕双的四公子轧道玩耍。有家世的上海人家是什么样子的;保姆是如何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的;上海小开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怎样的,都在他心里,比方裤缝要有一根筋,皮鞋要亮,手指甲缝不能有脏东西……还有,四公子教会他如何花钱。
“上海活宝”回头记
一个人的前史很难讲全讲真切,只能凭他自己说或听别人说。周立波自己讲在大可堂的淘气时,人们总是爆出大笑;譬如他说“那时写检查就像开支票。毕业那天老师把检查书统统还我,噢呦,有《家》《春》《秋》那么厚。”姐姐文文气气地说:“我们总是3个人被叫到学校去……我爸爸后来跟老师讲,你们开除他算了,我们也教育不好了。”
周立波后来因为打伤女友父亲的眼睛被押上法庭,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滑到谷底”。23岁的年轻人已小有名气,滑稽界称“上海活宝”,警车旁边许多戏迷就是证明:“让我们再看看周立波。”
出狱那天,他回到家里,满是人。他第一个要找的是母亲,找到小房间,母亲坐着。见到他,“哇”一声大哭,“她一口气总算舒了。”他的恋爱、结婚以至于后来种种波折,母亲都报以也只能报以清泪两行。
然而,就像他能从四公子身上学会花钱,周立波也能从学者身上汲取知识,从正派人身上学习做人。今天他转述由钱文忠教给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北人南人造酒的差别”、“温州瑞安和福鼎因何出美女”、“温州宗族械斗”,一套一套,栩栩如生。
80年代,周立波结交了京剧世家弟子关栋天。“一个驯兽师该做的,他都做了。”做生意时,周立波曾在某夜总会一年掷下200万元。终于有一天,他答应关大哥,从此不去了。“他对我,又像父亲又像兄长,可能是上海滩对我最重要的人。”
某一年生意纠葛,周立波避走武汉。走前他想,从此我就不是有钱人了,于是对关栋天说:“你陪我再到万宝大酒店吃顿鲍鱼鱼翅好 ?”关栋天陪他吃完,送他上火车。
“生意场上不缺他这么个人,舞台上缺他这样的人。”关栋天爱才,他一次次劝周立波重返舞台,“可是他不接茬。”今天他看着周立波站在舞台上,发出比美琪大戏院射灯更璀璨的强光,看着观众如痴如狂,笑意漾在脸上。更何况,直到今天,周立波还会像个孩子一样突然跑到他身边,向他耳语。
在周立波蹿出苗头、将红未红之时,是他以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周立波铺路,以个人名誉为他担保——从2006年第一场复出开始,关栋天陪他一路走来;同时帮衬着他的,是那些听上海滑稽戏长大的、如今头发多半白了的观众。
那一场,周立波几度失控泪涌。一次是唱起《再回首》;还有一次,是十多年未见的朋友上来献花,他一瞧,半头白发。
那一场,严顺开上得台来也哭了。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给金子,也不换。”
喜欢他,就爱护他
周立波第一次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正规场所,是2008年一次内部团拜会。那一场,他演了2小时55分钟,周立波望向站在舞台一侧的关栋天,大哥没有示意他停。
那一场,他表演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3位领导人态度的段子,对领导人性格的把握非常准确,台下的领导们也笑了。他也讲了股市的段子,比较到位。
此后,有过两次包场。但周立波感觉并不好,那些自愿买票来看他的观众,身体冲前坐,还没等他开口就笑了;拿了包场票进来的,抱着胳膊靠着椅背,冷眼看他耍宝:“不好笑嘛。”买票来的和拿票来的,分明是两类人——周立波从此有数,自己的观众在哪里。
上海人说:想要火,先起个蓬头(造势)。媒体渐渐知晓,前赴后继。官员学者也集结登场。显然,上海籍或在上海很多年的专家学者都为周立波的出现精神一振。余秋雨、钱文忠、李天纲的评说已被反复引用,包括那句比较吓人的“百年一遇”。
5月14日,上海市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郦国义在专家云集的“周立波脱口秀研讨会”上开首挑明两层意思:“大家都喜欢周立波;大家要爱护周立波。”
那次会上,程乃珊说,不要指责周立波俗。余秋雨还有个说法:不要老说周立波的成功是因为他“豁边”(出格)了,他不是因为说了大家不敢说的话才成功的。
郦国义告诉记者:以前广州有红火的音乐茶座,当年的朱哲琴就是在广州“扑通一百”歌厅唱《一个真实的故事》起步的。现在东北有二人转,湖南湖北有演艺秀,上海缺少具有地方特色、能登大雅之堂的演艺样式也有一阵了。几年前,曾经冒出过一个蔡嘎亮,因为商业纠纷半路夭折。虽然今天在沪上大浴场,这种民间有活儿的艺人并不少,也有很多类似周立波那样把生活当中的花絮拿来演绎的,但有的格调确实不高。说白了,周立波填补了上海娱乐文化这个缺,他的蹿红是市民娱乐所向。
“现在一些专家学者一定要把他拔高到代表什么文化、什么冲突,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郦国义说。
“焦菊隐有两段语录,他说戏剧表演的成功,关键是‘动作性的语言’和‘语言性的动作’;驾驭好这两者和两者的契合是话剧演员成功的关节点。这话他是说给演《雷雨》繁漪的女演员吕恩听的,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演繁漪最成功的女演员。我觉得这两句话可以移送给周立波,分析一下周立波的演出,成功的方面很可以用这两句话概括。”郦国义曾搬了椅子跟评论家毛时安一起坐在兰心大剧院看周氏火爆演出,当时也笑得无比开心,第二天一回味,其中有些便淡了。
他最欣赏的段子包括“门可罗雀”——“麻雀看到股市交易所一片泛绿,以为共青森林公园到了,以为延中绿地到了,统统扑上去;下午收市,扫地阿姨扫扫一畚箕麻雀”;还有“斜背保险带”——坐在副驾驶座,斜挎背包假装系了保险带,第二次被逮,因为背成另一个方向——这里面有小老百姓对付警察的小智慧、小乐趣。这些,都是有体温、有生气的东西,是接近侯宝林先生艺术高度的东西。他期望能有一个或几个滑稽界的“齐如山”出现,来辅佐人极聪明、悟性也高、但尚未成熟的周立波。
剧作家沙叶新对记者说:讽刺是喜剧的灵魂,没有讽刺,只能是笑笑罢了。当他听说上海滩出了个敢开政治玩笑的滑稽演员,略略生疑:“怎么可能是上海?”
上海籍的上帝会怎样说?“这浆糊捣得不错。看看再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