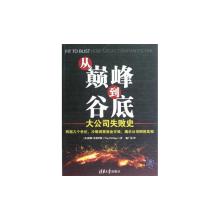人类学宗师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2009年走的,活了101岁。他结过三次婚,但没什么节外生枝的风流韵事,不像萨特。他的思想也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他俩道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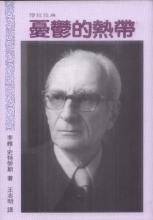
还是从《忧郁的热带》说起吧,只要提到李维史陀,就绕不开这本书。它在李维史陀所有的著作中独一无二、名气最大、读者最多。
上世纪50年代,巴黎普隆(Plon)出版社接受地理学家马洛里的建议,打算推出一套“人类的大地”丛书。马洛里自己写了一本关于北极考察的书,大概为了找一个地域的对应,觉得应该有一本以热带为背景的书,于是马洛里邀请李维史陀写一部巴西考察的非学术著作(李维史陀1935年到1939年曾在巴西做田野工作),就这样,李维史陀一鼓作气完成了《忧郁的热带》,成为“人类的大地”丛书的首批书目之一。当时李维史陀对自己的学术事业没有十足的信心,他日后坦承,若能料到自己有机会进入法兰西学院,他绝不会写这种没有学术分量的书籍。不务正业的“罪恶感”和对未来前途的“恐惧感”,反而让他下笔如有神助,他似乎豁出去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想到什么写什么,水到渠成。书一出版,好评如潮,巴黎纸贵。
这是一本李维史陀的回忆录,一本游记,一本文学作品,当然它也是一本人类学的里程碑之作—尽管,李维史陀始料未及。
《忧郁的热带》饱含了一个中年人对时间流逝的伤悼。李维史陀的敏感细腻,让人想到普鲁斯特;而他的悲观幽暗,又具有波德莱尔的气质。甚至在《忧郁的热带》这本书里,我们还看到了康拉德的影响。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毋庸置疑,因为它不是小说,法国龚古尔奖委员会特地印了一份公报,说明他们对于1955年未能把《忧郁的热带》列入考虑范畴而表示遗憾。
李维史陀是有不羁之才的,《忧郁的热带》全书带有挑衅口吻的第一句话是:“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这句爆炸性的开场白当然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实际上,他这本书,无疑是本旅行志,也不乏探险意味。上世纪中叶,巴黎上流社会流行一种贩卖异国情调的、肤浅的旅游文学,李维史陀意在与此风气划清界线。
我现在回过神来,朱天文为什么迷李维史陀。1996年我第一次去香港,买了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满纸都是李维史陀、福柯、小津、成濑巳喜男。后来我成了小津、成濑的忠实影迷,也读了一些福柯,却忽略了李维史陀。
最近读了《忧郁的热带》和《月的另一面:一位人类学家的日本观察》,激发了我对李维史陀的极大兴趣和无上崇敬。
李维史陀1977年至1988年,五访日本。他童年时收集很多浮世绘画片,还有其他日本手工艺品。他的童年和一部分的青少年时光,是在日本氛围里度过的。奇怪的是,成年后,他把日本忘却了或者说把日本搁置一边了。他去巴西( 《忧郁的热带》)、去美国、去印度、去其他国家。可就是没去日本。晚年,他返老还童,回归日本。五次到日本访问考察,走遍乡镇岛屿。他当然免不了欣赏樱花,学术演讲,社交应酬;也免不了参观博物馆、寺庙、神社;但主要时间都用来会晤织工、陶艺工匠、金匠、染工、木工、清酒师、厨师、糕饼师、漆匠。他着迷并尊重日本的手工艺。很巧,我之前读了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的几本书,沉浸在柳宗悦对日本民艺的寻访和描述之中,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对“手工劳作”的用心与用情。遗憾,李维史陀七老八十才去日本,写不动了,只是零星的演讲和概括。相信他和日本手工艺人的交流,一定留下不少笔记,但都没有成书,看不到完整的考察细节。
李维史陀的古典音乐修养不凡,他对肖邦和德彪西的评论,令人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里的阐述。他爱看的日本电影是沟口健二的,不是小津的,让我这个“小津迷”略感失望。他也为日本传统音乐所感动。日本米饭配烤海苔的味道,让他一再回味,如同普鲁斯特的“马德莲蛋糕”。是的,又是普鲁斯特!没有哪位学者比他更接近普鲁斯特了。
李维史陀很喜欢用弗洛伊德的术语“颠倒”,觉得日本是欧洲的“颠倒世界”。在李维史陀之前,葡萄牙神父弗洛伊斯和英国人张伯伦就注意到在不少方面日本人做事方法和欧洲人相反。譬如日本裁缝穿针时,以针孔就线,而不是拿线就针。古代日本,人们从右边上马而不是左边,等等。这种和欧洲的颠倒,也构成了一种对称。这与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有关吗?或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