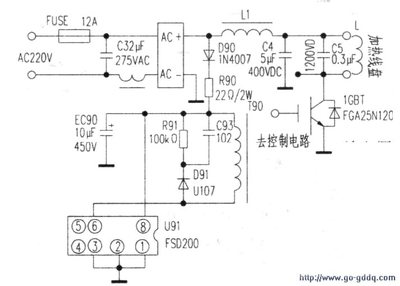对经济学的反思
山雨欲来风满楼。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将人类社会引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保八”到医改,从金融到流感,种种交锋与反思的弥漫,无不显示着各异的皮肤之下暗涌的阵阵悸动。三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中国的“大转型”;如今,世界的“大转型”似乎更已大幕初启。“改革”也在一夜之间,从中国人熟悉的发展之本,成为跨越国界的时尚。在现实世界的政经变幻中,我们何以居于现在?我们又怎样期待未来?中国与世界,在传统与现代化的交光互影中喷薄而出的问题与前景,也正为人们在历史的螺旋中捕捉自我展开了一扇立体的窗。
往事越千年,人类在危机中失去的,必将在社会的加快进步中获得补偿。这次危机给我们留下的,将是怎样一笔思想遗产?
每一次危机,总伴着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思考,从而成为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创新的契机,懂得这一点的人,才不会成为匆匆的过客;懂得这一点的民族,才能始终拥有未来。新中国岁足甲子,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中国正已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如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在世界历史的深邃星空中,找到属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星座?我们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什么?
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学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而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和利益格局最鲜明的体现。《周书》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站在世界大变局的大幕前,让我们拉开一扇立体的窗,展开探索的旅程,细梳云涌,伫看风行。
GDP真的那么重要吗?
谈经济必谈GDP,GDP的增长状况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这也许是经济学家圈子中最无争议的话题,GDP也是普通百姓讨论经济时最为顺口的词语。对GDP的一丝怀疑,最初也许源自坊间流传的许多对于GDP的玩笑,如果要实现“保八”的目标,其实只需要中国百万家庭的每对夫妻天天为彼此的家务劳动付费就可以了。而在笑料之余,仍然是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让我们反思,长期占据全球GDP排行榜首位的美国,不仅依然需要面对高自杀率和高犯罪率、城市环境恶化和国内种族冲突等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金融风暴面前也与任何一个以GDP观点看来的小国一样无能为力。这也让我们不禁反思,GDP真的那么值得我们相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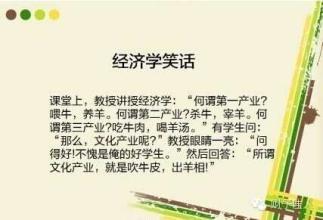
让我们首先回到亚当斯密。GDP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于“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s)的论述。如今大众所最为熟悉的GDP,不过只是对广泛意义的国民财富的一种数学度量方式而已。事实上,我们需要反思的,还并不仅仅是GDP作为一种度量方式在技术上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而更需要重新审视以GDP作为导向的发展观念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GDP是可信的吗
首先,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是否一定能够可靠的保证人们迈向更为幸福的生活状态?答案至少是不确定的。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言,财富的积累并不可能自动导致人类的幸福,相反,正是内心的平静,才可能最终让人们经由财富的积累而实现对幸福感的体认。当代最具影响的有关社会财富积累与人类幸福感的研究源自于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1974年,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文章“经济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显著的改善吗?”(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正式向现代工业社会以GDP为发展目标的经济观念发起挑战。伊斯特林以针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大量历史数据,指出实际经济中人均收入的绝对增长无法必然导致人类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甚至会造成相反的效果,从而首次在实证经济研究的层次上,为人们对客观财富增长的过分迷信提出了质疑。事实上,在更早时期的规范经济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中,对幸福与财富的争论虽然未能成为思想讨论的绝对主流,但是一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其中还包括至今仍在心理学界具有主流影响的,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这一理论指出,从最初的生理(Physical)和安全(Safety)需要开始,人类的需要逐渐上升到社会(Social)、尊严(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层级,只有在较低的需要层次上,人类的主观幸福感才与财富的绝对量有明确的正向关系;而在较高的需要层级,尤其是自我实现的价值层面上,财富本身很难对人类幸福感的提升造成直接影响。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为财富和幸福感中的不确定关系赋予了微观的基础,正是因为财富只能对应人类的相对较低层次的需求,它永远无法成为人类全面幸福的一种有效的度量指标。
更为实际的,我们还需要理性面对经济发展中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念的另一个严肃问题,即其本身对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违背性。必须意识到,与上述讨论中的“财富”概念不同,GDP所衡量的并不是个体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是在某一段确定时期内的财富“总流量”。对这一理解的澄清,就自然会把人们带入公平和历史的视野,也让人们更清晰的观察到单一的GDP发展观与全面和谐发展的冲突性。一方面,在计算GDP“总量”的过程中,统计部门很难精确的为每个社会个体的财富作出准确的度量,因此,人们永远无法判断,GDP总量的上升,是否是以牺牲某一些个别社会群体的财富或利益作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在考虑GDP“流量”的过程中,人们也无需涉及当期之后的任意一个时刻中的财富的可能状态,因此也永远无法知晓,我们是否应该在当期GDP的繁华中,减去那些潜在的透支未来的成本?而且,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H. Stiglitz)所言,GDP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美国的“监狱GDP”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前,美国处于正式关押或保释羁押状态的监狱人口已经接近700万人,在每个时刻,大约每30个成年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监狱。而美国全国监狱系统这个“超级大公司”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财富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至今还继续投入每年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这样庞大的“监狱GDP”,由单纯的GDP发展目标而抛给社会的庞大问题,难道真的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吗?
结束对美国监狱GDP的参观,让我们转身面对今天的中国。诚然,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都对有朝一日中国在GDP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全面超过美国充满信心,甚至进一步预测出GDP总量和人均GDP超过美国的准确时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是,给定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这样的GDP规模,真的是中国社会的公平环境能够支持的吗?又真的是全球的资源基础能够保证的吗?即使中国在GDP的意义上成为下一个美国,又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当前的美国所面对的诸多问题,甚至是对于全世界经济都难于解决的问题?最终,世界第一的人均GDP,又一定能保证中国大众享有真正的全面幸福吗?
GDP之外的人类发展
其实,给定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念与人类全面幸福发展的内在矛盾性,而又因为幸福这一概念本身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必然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务实的态度,寻找另一些我们可以期待和度量的度量方式和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便是在度量经济发展意义上的一种尝试。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并不复杂,正是考虑到人均GDP在衡量经济发展维度中的单一化缺陷,而在GDP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健康和教育的度量,以这三个指标共同衡量人类的生活质量。其中,健康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则以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共同衡量。每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会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意义上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对全球社会发展进行相对多元化的评估和分析。而在2006年,由一些经济学家发起的“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进一步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地球幸福度指数”(Happy Planet Index),进一步将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考量,并首次在指数中完全去除了GDP这一传统指标。地球幸福度指数主要包括主观幸福度,健康水平和人均生态资源依赖量(Ecological Footprint)三个组成要素。可见,这一衡量指标已经越来越接近人们所真正期待的,对可持续的幸福发展的全面度量要求。
让我们透过这些更为多元化的发展度量方式,进一步思考我们未来可取的发展目标。不难发现,全民健康,既是各种多元化指标都引入度量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正是在真实的政策制定和发展规划中最贴近大众民生,也最具有社会全面影响的一个发展维度。从传统GDP发展观的传承意义上,汗牛充栋的经济学和医学研究已经充分验证了GDP发展与全民健康水平提高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诚然,我们很难单一的判定这两者之间究竟孰因孰果,最大的可能其实是两者相互影响的因果循环;但是,没有稳步增长的GDP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发展,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这让GDP增长成为全民健康水平提高的一个必要条件,也让全民健康的发展目标自动涵盖传统的GDP发展观念。而更重要的是,追求全民健康的发展观能够更有效地包容GDP之外的,多元化的人类发展目标。首先,健康状态本身始终是针对个体和存量的概念,这让健康指标能够自然纳入更多的有关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更进一步,在我们难以获得一个更为准确而被普遍接受的,直接度量人类“幸福感”的标准之时,健康水平,作为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正是最有可能衡量人类全面福利的一种标志。这也是由人类健康自然的双重属性,即其生理性和心理性的融合而决定的。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中所积极倡导的,人类发展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追求能够享有的真实的自由,而最重要的一种“真实自由”便是健康和对死亡的避免。所以,森把健康认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它可以从根本的意义上,成为使人们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和成为他们想成为的状态的基础,最终让人们选择他们的有价值、有质量的生活。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传统GDP追求的只是单纯的生活中的“数量”(Quantity of Life),全民健康则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了生命中的“质量”(Quality of Life)。
而且,正像“健康”这一词语本身所蕴含的直接意义和引申意义一样,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观念中的“医疗”概念,也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概念。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在成立之初的1946年,就在《世界卫生组织法》中明确提出了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或对疾病的防止,而是生理和心理的全面适宜,以及整体社会的福祉和完美状态”。对全民健康的关注,不但能够促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忽视健康价值,尤其是忽视健康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价值的普遍观念的反思,而且还能够激励人们更多的以健康作为标尺来衡量经济政策的效果。这样的反思,能够更有效的促进形成健康的生产和消费观念,从而导向更为健康的整体发展观。此外,还由于健康对于人类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对健康的关注往往比其他发展目标被赋予了更多的民生和公平意涵。从政府到大众,从医生到患者,期待健康,无疑是毫无争议的共同追求。如果能够充分积聚各个社会群体对健康的共识,全民拧成一股绳,共同抵抗疾病和不健康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风险,不仅能够极大的促进医学意义上的全民健康,更有可能成为解决广泛存在的官民矛盾和医患矛盾的一个契机,从而导向更为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从根本意义上,正因为健康二字衡量的是人类自身,而非任何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衡量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整体,而非任何人类发展的侧面或它们的简单加总:关注健康,便更可能成为我们当代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经济理念下的明确的追求。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那样,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这一健康水平的提高,不但意味着与人们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相关的生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与社会风貌、可持续发展,以及全民幸福感相关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才能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的优越性,最终从GDP导向的单一发展逐渐向以全民幸福为导向的多元化发展而靠拢。
加法是可信的吗?
不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个人的成长史,加法,都可谓是我们从蒙昧状态开始认识世界中各种关系的的最初一步。而在当代经济社会中,个人消费之和便是社会总消费,各省GDP相加便得到全国一年经济发展的总成果,加法的应用也是如此自然而没有争议。但是,如今的全球金融风暴,几乎没有一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在危机之前向公众发出任何危险的信号。这在让全球经济学家反思经济学中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一几乎是天经地义正确的基础运算。经济学中的加法,真的是如此可信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怀疑加法?这需要从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盛行一时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加总理论开始谈起。以卢卡斯(Lucas)和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理性预期革命”,这次革命也成为了如今占据主流的宏观经济思想的发源。他们指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把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先验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GDP、利率上,单纯的考虑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这些变量及其关系的影响,却忽略了经济中真正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对于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因此是不合理的。针对这样的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体最优化决策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经济生活中的人们被抽象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通过对他的微观经济决策的分析,再进行一次直接的加总,便能够得到对宏观经济中各种因素的真正描述。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这样的宏观分析直接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个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因此是可靠而有“基础”的,在历史上,他们的努力也正被称为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如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测,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系列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之上的。
但是,任何一个从未学习过现代经济学的人,也可以从上面这段通俗的描述中看出破绽,这个破绽便在于对于加法的怀疑。对于一个假设意义上的“代表性”个人经济活动的直接加法,是否真能如此自然地得到对整体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描述?首先,在如今大多数可以操作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性都已经被大刀阔斧的砍去,我们处理的其实仅仅是一个同质性的人,这样的加法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对于一个人的乘法;然后,也是更重要的,如社会加总这样的复杂过程,是否蕴含着一般意义的加法所不能涵盖的新的要素?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的合作效应,相互制衡,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统计相关性,都可能让一加一不再等于二。从而,如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所解释和预测的,很可能只是“一群代表性人”的问题,而远远不是“一个”整体经济的问题。事实上,金融风暴,乃至全球变暖、核扩散,这是成千上万各异的人所组成一个整体社会经济机制所面临的“整体”问题,而不是一大群相似的兔子或蚂蚁所面临的“群体”问题。
更进一步,对加法的过分自信,不仅仅显性存在于当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和金融学思想中,而更隐性存在于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经济思想脉络的,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从个人最优到社会大同这一过程的自然性的过分自信。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否认“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应否认在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中,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当前所知的,让经济实现效率运行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亚当斯密本人从未说过,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否能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体化,他也无法想象由于当代世界的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直接冲击人类整体的经济问题。事实上,在亚当斯密的年代,经济学本身尚未形成微观与宏观的分野,也并未出现任何对于市场有效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如今,当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边界已经形成,而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这些词语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时髦的时候,人们往往已经熟于争论在微观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市场和政府究竟何者更为有效,却往往忽视了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这个“加法”过程本身所带有的巨大外部性,这也正是社会意义上的加法所带来的质变所在。全球金融风暴本身便是最为直接的例子。显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金融风暴的发生,对金融风暴的规避,自然可以被认为是每个人效用函数中的一部分。但是,任何一个人的个人行动,都不可能直接导致金融风暴发生或者组织金融风暴。因此,如果没有任何社会合作的整体力量的推动,那么每个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最优行为便依然是按照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的方式进行行动,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华尔街的每一个金融衍生品模型都可能已经无可挑剔,但是它们却永远无法分散在这些模型共同起作用时所产生的新的宏观风险。这样的逻辑类似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生物学教授哈丁(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但又远远比单纯的公地悲剧更为复杂。戏剧性的是,这一由自然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如今最容易被看到的场合是经济学教科书,却又未能唤起经济学家们在思想层面真正的重视。诚然,个人所关注的经济问题,固然也是社会整体需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在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加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应该存在的加法,已经被融入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更多元素,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单纯意义上的简单相加了。这样的加法,显然不是“看不见的手”这单独的市场经济力量所能够完成的。
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的加法,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应当是一个经济整体,而不是单纯的一群人。遗憾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却无法自动完成这一任务。这样的期望,便也为经济世界中的加法赋予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层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不论是经济学本身,还是大众普遍应用的社会经济思想,我们都更需要一种面向社会的加法,而不是面向个人的加法。这也正是当前的金融风暴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所提出的迫切要求。面向社会整体,并非意味着否定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要以国家计划的方式来代替个人作出每一个经济决策,而是要求在个人最优决策的同时,以社会整体的立场来面对个人选择所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的宏观经济问题。自然,这便要求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需要对“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力量进行必要的社会补充。一方面,它要求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确,在从纯粹市场经济中的个人选择到社会整体福利的跨越中,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会产生何种不同形式的新问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微观和宏观的鸿沟搭建一座“中观经济学”的桥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市场经济之外的社会力量,在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同时,建立真正有效的政府、国家,甚至国际合作机制,来补充市场经济对于解决大范围宏观问题的乏力。这样的思路,也正是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