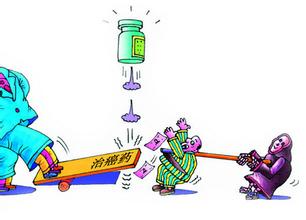系列专题:《金融异术》
【宣传语】
华尔街13位顶尖技术分析大师的秘诀披露
彰显技术分析超凡绝群的魅力
【卖点】
u 作者罗闻全(Andrew W.Lo),世界著名金融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华人,被《商业周刊》评为金融学术界最有前途的三颗新星之一,华人中最顶尖的金融学者
u 汇集了华尔街13位顶尖技术分析大师的口述实录,
书名: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
作者:贾斯米娜8226;哈桑霍德齐克、罗闻全
书号:978-7-111-30767-9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
罗闻全和贾斯米娜8226;哈桑霍德齐克认为,要真正认识技术分析,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自去接触这个领域内最有权威的实践者。为此,作者对13位当今世界顶级技术分析大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² 61548; 拉尔夫8226;阿卡姆波拉(Ralph Acampora)
² 61548; 拉斯洛8226;比利伊(Laszlo Birinyi)
² 61548; 沃尔特8226;迪莫尔(Walter Deemer)
² 61548; 保罗8226;德斯蒙德(Paul Desmond)
² 61548; 吉尔8226;杜达克(Gail Dudack)
² 61548; 罗伯特8226;法莱尔(Robert Farrell)
² 61548; 伊安8226;麦克艾维特(Ian McAvity)
² 61548; 约翰8226;墨菲(John J. Murphy)
² 61548; 小罗伯特8226;鲁格劳特8226;普菜切特(Robert R. Prechter Jr.)
² 61548; 琳达8226;布拉福德8226;拉斯奇克(Linda Bradford Raschke)
² 61548; 艾伦8226;肖(Alan R.Shaw)
² 61548; 安东尼8226;塔贝尔(Anthony W. Tabell)
² 61548; 史丹8226;温斯坦(Stan Weinstein)
这些实践者向我们分析了他们最喜爱的形态、指标、策略及其运用,毫无保留地诠释了他们的成功秘诀。对几位技术分析大师进行的采访坦率而生动,不仅让我们有幸重温他们的职业生涯,也让我们一睹创造力、情感和直觉在技术分析中的奇妙作用。
【作者简介】
罗闻全(Andrew W. Lo),一个从生物学进化论解释人类行为选择的天才,华人,罗伯特C.默顿(RobertC.Merton)在MIT教的最出众的学生之一。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麻省理工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世界著名金融学家,金融工程学界的领军人物,生物金融学创始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理论、金融信息技术、风险管理、证券组合管理以及金融统计学。他尤其擅长金融工程及计算金融,是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的创建人之一,并使该实验室成为全美金融工程界最高水平的代表。他因不断把金融工程的研究前沿应用于金融实践而在学术界和华尔街享有盛誉, 于1998年被《商业周刊》评为金融学术界最有前途的三颗新星之一,堪称华人中最顶尖的金融学者。
他与约翰8226;坎贝尔(John Campbell)、克雷格8226;麦(Craig Mackinlay)合著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获1997年度保罗8226;萨缪尔森奖;还著有《非随机漫步华尔街》(A Non-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1998)一书,阐述了非随机性在预测股市绩效方面的影响。他是马塞诸塞州对冲基金公司AlphaSimplex 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贾斯米娜8226;哈桑霍德齐克(Jasmina Hasanhodzic),AlphaSimplex集团研究员,负责数量投资策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点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她曾在《投资管理杂志》(Journal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和《机构投资者的系统风险》(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等刊物中发表多篇研究成果。
【业界推荐】
《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以全新视角诠释了技术分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无论对于金融从业人员,还是学术界人士,这本书都将帮助他们认识技术分析的实质,探究技术分析何以在当今市场如此意义非凡的根源所在。毫无疑问,这本妙趣横生的作品,将会给您无限的启发。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莫林·奥哈拉(Maureen O’Hara)
金融学名誉教授
技术型交易普遍存在于金融市场,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金融市场的某些非常规现象,因而,也是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罗闻全和哈桑霍德齐克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探索这个还不为大多数人真正了解的领域,而他们的成果同样令人称道。
——马塞诸塞州布兰迪斯国际商学院(Brande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教导主任
卡罗尔·奥斯勒(Carol Osler)
前言
如果两位初探技术分析殿堂的业余爱好者和14位当今顶级技术分析师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有效市场、随机游走假设和数量金融学的其他原理,谈论这些技术分析行当的细枝末节,那么,您认为会发生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声明:我们不敢担保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于技术分析实务操作这个领域,我们本来就是门外汉,当然,也就不是业内经常说的“技术分析师”。对于那些熟悉我们的研究或是技术分析的人来说,这应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对这门手艺以及技术分析这种文化的迷恋,尤其是它们不同于数量分析的特色,促使我们走上这条充满惊奇的探索之路。能有机会和这些业内最具天赋、最优雅、最执著的人共享他们的知识与智慧,既是我们的兴趣使然,也是我们的无上荣幸。1事实上,我们已经对技术分析有些感悟,因为专业人士已经在实践中无数次地演练过这些理论。
但是,我们这些理论者与这些实践家的探索之路到底会怎样交汇到一起呢?毕竟,技术分析师既不是学术讲堂的常客,也不会经常和金融学的教授和学生打成一片。这样的分歧很容易理解:大多数学术界人士还觉得图表纯属子虚乌有之物,因而对它们嗤之以鼻,在很多学者的眼里,技术分析之于财务分析,就如同天文学和宇宙学一样,相去甚远。不过,有些技术分析师偶尔也会用到占卜术(见Weingarten,1996)。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似乎帮不上什么忙。
尽管存在种种疑虑,但依然有很多无畏的学者凭借无尽的激情探究着技术分析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有些人只是出于渴望和好奇,但更多的人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随机游走假设与现实数据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分歧。而这些研究也为我们认识技术分析的优点和缺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2
随机游走的衰亡
我们踏进这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但却如同地狱般的预测领地的第一步,源于20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讨论对象是随机游走假设(random walk),即:通过以往的股价可以预测到未来股价的变动。而这篇论文则用每周的股票回报率数据彻底推翻了这一论点(Lo和Mackinlay,1988)。对于技术分析而言,无论怎样强调随机游走假设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而这篇论文则意味着,以前的股价与以后的股价毫无关联。假如股价变动是随机的,那么就不可能用历史价格来预测未来价格,因此,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上的几何模型也不包含任何对未来有价值的信息。1985年,在为撰写这篇论文开始调查研究时,随机游走假设还被金融学术界的高层人士奉为不可挑战的真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很多著名的实证性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为“弱有效”(Robert,1967),也就是说,历史价格不能用于预测未来的价格变动。3尽管某些研究确实取得了可以驳斥随机游走假设的证据(Cowles和Jones,1937),但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都归结为统计上的小概率事件,或是在考虑交易成本因素时便成为毫无经济意义的不规则波动(Cowles,1960)。比如说,在对1956年到1962年期间美股收益率的“走势”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之后,法玛(Doyne Farmer,1965)得到如下结论:“……无论是从投资角度,还是从统计角度看,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Lo和Mackinlay)才决定重新审视随机游走假设。由于以往的研究并不能彻底推翻随机游走假设,因此,我们猜想,也许只有通过更敏感的统计研究,才能揭示出否定纯随机性的细微的显著性偏离。按照统计推断的术语,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检验模型,如果随机游走论确实不成立,我们就可能借助这个模型去推翻它。但现在回过头看,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如此严格的检验。1962年到1985年期间每股周收益率对随机游走假设的全盘推翻也说明,如此强大的统计检验确实没有必要。实际上,只要借助于一次自相关系数,就完全可以否定随机游走假设。我们按照相同权重对美股周回报率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一次自相关系数(firstorder 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只有30%!这个结果让我们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因此,在1986年11月的学术会议上最终宣布这一研究结果之前,我们反复核对了检验过程,确保不存在任何编码误差。铺天盖地的研究怎么能对如此显著的反面证据视而不见,然后,又把一个在本质上就不成立的假设当作不朽的哲理灌输给学生呢?
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统计结论与此前诸多研究的成果是完全矛盾的,这促使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以探究矛盾的根源。这些研究收录在罗闻全和克雷格·麦金利(Craig MacKinlay)合著的《华尔街的非随机游走》一书中。经过这番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包括核对统计方法的精确性,对非同步价格(nonsynchronous price)带来的潜在偏差进行量化,对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设的数据进行调查,并由此推导出较大的正交叉自相关系数(cross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以及先导/滞后效应(leadlag effect),我们却只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却无法解释这些违背随机游走假设的数据。”
这些研究结果刺激了我们,促使我们对技术分析展开一场更系统的研究,也为实施本书所述的采访铺平了道路。
文化差异
罗闻全和麦金利的成果不仅为我们认识技术分析和其他价格预测模型敞开了大门,也为我们了解一直让学术界饱受折磨的文化偏差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验证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我们终于认识到,业界对随机游走假设的广泛支持与实证结论之间的巨大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一个最常见的误解——把随机游走假设等同于有效市场假设,以及经济学家对后者近乎宗教一般的顶礼膜拜……但现在却突然发现,正统经济学者接受的教育总是让我们(当然还有我们的同道者)不自觉地戴上有效市场假设这一传统规则造就的有色眼镜,去选择性地解读数据。显而易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实证分析,而是在于其他因素给这些研究成果带来的干扰,比如说利润空间的无界性和投资者的非理性等非完美的市场前提……对于随机游走假设的合理性,尽管我们都感觉像是一团迷雾,不过,一旦获得各个角度的实证依据,我们就开始走出混沌,慢慢地拨开迷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一步步地接近问题的真谛。”|!---page split---|
不过,我们并不是第一批想到研究金融界文化差异问题的先驱者,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在具有自传色彩的《投机生涯》(The 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一书中,以轻松幽默的文笔阐述了某些造成这种偏见的因素。当随机游走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就曾经写道(Niederhoffer,1997年,第270页):
他们终于找到一个经典表达方式来阐述这一理论及其追随者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绝对会流芳百世。创建这个理论的团队只有四位令人尊敬的金融学研究生和两位金融学教授,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就绝对令人仰止,他们完全有理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资格去竞争诺贝尔奖。但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似乎有点离经叛道,连他们自己也像初次约会的小伙子一样,感到惴惴不安。这个精英团队的研究对象是成交量对股价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在哈斯凯尔大厦(Haskell Hall)三楼图书馆的楼梯上,遇见了这六个人,他们站在楼梯平台上,正在讨论一些计算机打印文件。他们的声音反射到借助建筑物的石壁上,飘到我的耳朵里。其中一个学生指着打印文件质问教授:“好吧,假如我们真得出相反结论怎么办?那我们不就成了怪物吗?但可以肯定的是,结论肯定和随机游走模型不一样。”年轻的教授回答:“别着急,我们迟早能找到方法解决这些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事。”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六个科学家为了寻求真理,居然可以做到如此的开诚布公。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你们对自己的研究这么坦率,真让我羡慕,让人兴奋。”在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满怀热情。不过,我得到的回应却是冷眼。
尽管这种文化差异也许能解释当前对技术分析的看法和怀疑,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却是根本性的。毕竟,技术分析师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其他人。因此,说到误解技术分析师,其实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因为分析师说的完全是外星球语言。要理解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技术分析师撰写的典型市场评论:
支撑线与阻力线并存,再加上位于两线之间时的1/3回调(retracement)参数参量(在股票接近支撑线位置时做多,因此,止损点应位于该支撑线下方一点,两者间距离即为做多的潜在风险,如果上方阻力线和买进价的差距是潜在风险的三倍或更大,则选择进场),表明近期存在强大的买卖力量。
对大多数研究数量经济学和投资学的人来说,这段话几乎就是废话,甚至可以说是玩笑,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这些话。与上面描述不同的是,我们在金融学刊物上可能会看到的描述:
前12自相关系数的幅度及其下跌趋势,再加上博克斯皮尔斯卡埃方检验(BoxPierce)Q统计量的统计显著性,表明股票收益率中存在明显的预测元素。
实际上,这两段话说的是一回事:使用历史股价,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短期价格的变动。但由于这两段话都充斥了专业术语,因此,它们引出的回应也就完全因人而异了。当然,两段话都隐含利用预测性的方法,尽管这种预测性相去甚远。语义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两段话的作者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现,对方的观点能为己所用。
指本书的两位作者。——译者注当然,这两个假设性论述仅仅是学者和技术分析师在工具和逻辑上的缩影,但它却凸显技术分析师和学术界之间的鸿沟,以及把两者融汇到一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那就是:必须找到一个相互理解、分享思维的共同语言。这也揭示出我们进行这些访谈的第二个原因:给这些当今顶级技术分析大师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但采访范围则严格限制在两个具有明显数量经济背景的外部人设计的问题范围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催化学术界和分析师之间的沟通机制,让他们通过分享和互补实现互惠互利。比如说,技术分析师也许会发现,统计推理技术的最新发展能帮助他们从诸多数据识别出纯偶然因素形成的乱真模式,从而减少他们所依附的“误证”(false positive)现象,提高预测的总体准确度。同样,金融学家可能也会发现,技术性交易规则中也包含着某些可以类比统计推理技术的近似性规律,从而为他们认识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提供依据;同时,历史价格中相对简单的几何分布图形恰恰可以用超级简单的方式模拟出高度复杂的经济均衡模型。

程序化技术分析
促使我们撰写本书的最后一个动机则是Lo、Mamaysky和Wang(2000)的一项研究,我们收集了美股个股在30年期间的回报率数据,从而对头肩形(Head and Shoulders)和双底形(Double Bottoms)等10个技术分析模型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在实验方法的设计过程中,我们(Lo、Mamaysky和Wang)就充分意识到,首先,我们绝对不是从事实务操作的技术分析师,也没有聘请技术分析师专门为我们的研究设计识别历史数据的技术模型。因为,我们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即“自动化技术分析”——通过简单的数学语言描述每一个股价图表,从而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设计成软件,然后,利用这种依据个别数据形成的软件处理大批量数据。例如,我们可以把头肩形定义为三个局部极大点(local maxima,头部)和两个极小最小点(local minima,底部)相互间隔形成的价格序列,其中,三个极大点高度基本相同,两个极小点的高度也基本相同,但极大点的高度超过极小点的高度(这样,将两个肩部的底部连接起来,就可以画出一条“颈线”)。
ⅪⅫ 通过这些简单的数学定义和灵活有效的非线性曲线模拟法(即非参数核回归方法/nonparametric kernel regression),我们可以省却冗长费力的过程,让100只股票在30年内每次出现的每一种形态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之后,我们再提出如下简单的统计问题:利用事后模型(post pattern)得到的股票收益是否与随机选取的股票有所不同?如果是的话,像头肩形这样的股价形态是否能为预测未来收益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不能的话,是否可以说,这些模型不过是纯粹的随机噪声,而不能为我们预见未来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研究结果令人震惊。针对纽约证交所上市股票进行的研究,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一片混乱:有些股票在这10种分布形态中表现出明显的统计显著性,但也有一些股票对任何分布形态均不具有显著性。不过,纳斯达克的股票却给我们带来全然不同的结果:所有这10种形态均表现出统计显著性,这就是说,所有这10种分布形态都包含有可预见未来的增量信息。尽管这些所谓的“增量信息”并不一定像大多数技术分析师说的那样,可以用来提炼出实现赢利的交易策略,但这些结论完全可以说明,技术性指标确实能增加投资过程的价值。而这些方法所揭示出的诸多可能性也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研究表明,可以利用我们所采用的程序化运算等模拟技术改善技术分析,而头肩形和三角形之类的传统形态,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肯定不是最优化的。进一步讲,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出“最优化形态”,识别出存在于财务时序数据中的某种特有现象,比如说用于鉴别随机波动的优化图形。此外,用于识别统计异常的优化形态也未必能实现交易利润的最大化,反之亦然。这些因素也许会引导我们在技术分析框架内创造一个全新的分支——通过选择合理的形态识别运算规则,实现目标函数的最优化。
要了解这个技术分析的新兴分支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首先要追溯灵感、动机和创新的根源。而这正是我们情愿被看做外行人而去采访这些顶级技术分析大师、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的缘故。
采访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技术分析大师中,每个人都才华横溢,极富理性,思维开阔,并对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们当中,尽管很多成功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耐心宣传自己的主见,尽量避免使用深奥莫测的技术术语,可以抵消投资者对他们的大部分偏见,但突出非常规因素显然不是技术分析师让市场认识他们的最佳途径。
我们所采访的大多数技术分析师都承认,在他们所从事的技术分析实践中,10%到50%的工作是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举个例子,虽然拉斯洛·比利伊认为自己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程序化计算,极少包含直觉性因素,但他的实务操作却体现出明显的直觉性。在确定决策模型及其成分的过程中,主观判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约翰·墨菲的话:“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某个指标,而是如何把这些指标组合到一起。”在实现这个合成的过程中,最成功的人,注定是那些通过实践深刻领悟经济和市场运行模式的人。
还有几位技术分析师认为,把所有支离破碎的信息整合到一起,并转化为价格分析的能力,绝对不是可以轻易学到的。正如墨菲所说的那样,“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我自己是怎样做的。我自己也是通过不断的观察,在零碎分散的信息中,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种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技能也许可以解释,这些实务操作者为什么在分享知识、他们所开发的分析工具和投资策略等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如何从个案推导出规律,把局部拼接成整体,显然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方法。每个人都会以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排斥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实际上,某些技术分析师往往能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做到最好——琳达·布拉福德·拉斯奇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从来不看电视,也不读《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人则喜欢借助基础面、经济和政治要素进行技术分析。显然,这些技术分析师在个人类型方面的表现多种多样,他们中既有成功的交易员(拉斯奇克和温斯坦)、投资教育家(墨菲和阿卡姆波拉)、长期投资者(德斯蒙德和迪默)、艺术型技术分析师(麦克艾维特)、高度折中派技术分析师(杜达克)、历史学家(肖和阿卡姆波拉)和以长期市场为主题的财经作家(法莱尔),也有一些人则自我标榜为市场分析师而不是技术分析师(法莱尔和比利伊),他们之间的差异之大,令人称奇,而他们在采访中的回答甚至是语气,都有着天壤之别。
这些结论揭示出这些顶级技术分析师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他们的观点还是方法,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异质性,而这也为我们解释技术分析对金融界缺乏足够影响力做出了间接回答。由于缺乏一个能被所有实务者广泛认同的统一的标准化知识体系,因此,技术分析自然难以实现普及。尽管市场技术分析学会(MTA)推出注册市场技术分析师(Chartered Market Technician,CMT),引导我们在正确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但正如接受采访者强调的那样,在实务操作中,技术分析师仍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艺术性和主观性。例如,在回答“技术分析领域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则是否给您带来困扰”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反应就相去甚远,既有人认为“这确实是最让我头疼的事”,也有人表示,“虽然麻烦,但技术分析也有严格的规则可循”。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我们得到的答案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对问题的理解——尽管确实存在某些可以传授的规则,但规则的结合以及对结果的解释,却依赖于操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感受。因此,这样的规则远非严格而不可动摇。基于这样的情况,假如技术分析继续沿着目前方向发展下去,以日趋精确的客观计量数字取代人本化的技术分析师,显然还需假以时日。法莱尔说,“这还是一个人的游戏。”
正如艾伦·肖所言,好的实务者虽然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但却未必提出正确的答案。他们怎么知道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史为鉴。一个亲身经历或者至少研究过牛市和熊市的技术分析师,只要做到理性面对,冷静思考,就能发掘出当下潮流和以往经历之间的联系。而历史总是倾向于不断地重复自己,因此,这就能让他们把关注点集中到正确的方向上。那些一直试图对技术分析不断解剖与合成的学者,实际上颇有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味道。
显而易见,接受我们采访的技术分析师多感到困惑不已:他们的技艺并没有得到机构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约翰·墨菲和保罗·德斯蒙德坦然承认,他们对技术分析明显逊色于其他财务分析方法的现状倍感失望,而拉尔夫·阿卡姆波拉在推广MTA注册市场技术分析师方面的不懈努力,罗伯特·法莱尔和拉斯洛·比利伊拒绝标榜为“技术分析师”以及比利伊所写的《技术分析的失败》(Failure of Technical Analysis)一书,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外界对技术分析领域的怀疑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这些最成功的顶级分析师之所以甘愿在百忙中抽出三个小时接受采访,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显示出,他们非常希望业界能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心声。
这些顶级技术分析实践者并不否认人们对技术分析领域的广泛质疑,因此,在和我们的沟通中,他们敞开心扉,坦言他们对学术界以行为金融学为手段进行的技术分析“再造”。现在很多情况下,学术界的定义和技术实践之间密切相关,相互借鉴。例如,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提出的“典型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1974),就反映了技术分析师对借鉴历史现象认识当下现实的重视。4不过,尽管有些研究试图“推倒重来”,重新打造技术分析的权威性,但技术分析师还是对这项吸引人们关注技术分析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更希望以此来赢得期待已久的尊严。
崭新的起点
既然我们是才开始从学术角度出发来探索技术分析的诸多方面,那么,我们还不能说学术界和技术分析师之间到底能找到哪些共同点。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些采访和我们的不懈努力,找到这样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坚信,融合各自的知识体系,调和这两个貌似对立的思维模式,注定会让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受益。
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技术分析不以为然,技术分析师也对学究式研究的原理和结构嗤之以鼻。但是,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宇宙,而是在于我们自己……”虽然要求我们这些学者去研究占星术有点过分,就像我们不能要求技术分析师去证明学术理论原则一样,但我们还是认为,这两个派别之间完全可以实现更有意义的对话,因此,我们更希望这些采访能成为此类对话的新起点。
ⅩⅤ注释:
1本书中的采访是在2004年到2005年上半年期间进行的,因此,被采访人针对当前事件提到的资料也应在该背景下进行解释。
2相关案例包括:杰克·特雷诺(Jack Treynor)和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on)(1985),Pruitt和White,Neftci(1991),Pau, R N(1991),Brock、 Lakonishok 和LeBaron(1992),Neely、Weller和Dittmar(1997),Neely和Weller(1998),Osler和Chang(1994),Taylor(1994),Osler和Chang(1995),Allen 和Karjalainen(1999),Lo、Mamaysky和Wang(2000)。
3相关案例包括:Cowles, A, & Jones, H (1937),Kendall(1953),Osborn(1959,1962),Roberts(1959,1967),Larson(1960),Cowles(1960),Working(1960),Alexdander(1963),Granger和Morgenstern(1963),Mandelbrot(1963),Fama(1965),Fama和Blume(1966)。
4实际上,所有参与者都非常重视对市场历史的研究。拉斯洛·比利伊甚至收集和分析了以往70年主要报纸杂志的相关文章。 ⅩⅦⅩ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