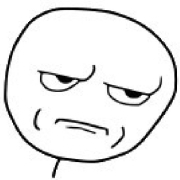系列专题:《金融异术》
第一章
拉尔夫·阿卡姆波拉(Ralph JAcampora)在从事技术分析时,你必须要学会兼收并蓄,因为你的方法总会有无效的时候,如果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你就是在自取灭亡。在40年的从业实践中,拉尔夫·阿卡姆波拉始终在当代技术分析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拉尔夫是纽约金融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Finance,NYIF)技术分析专业主任。在进入纽约金融学院之前,他曾担任武士权益市场(Knight Equity Markets)的技术研究主任,并在保德信证券集团(Prudential Equity Group)担任技术分析主任达15年之久。此外,拉尔夫还曾在多家顶级金融企业任职,包括基德·皮博迪(Kidder Peabody)和史密斯·巴内(Smith Barney)证券公司。
作为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技术分析大师,阿卡姆波拉不仅是诸多大型商业新闻媒体的常客,还经常在全国性金融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技术分析师排名中名列前茅。阿卡姆波拉拥有注册市场技术分析师(Chartered Market Technician)资格,这一资质是他一手创建的,并得到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NASD,即现在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简称FINRA)的认可,目前,技术分析师已经获得与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平起平坐的地位。 阿卡姆波拉是1970年创建的市场分析师协会创始人之一,曾一度担任该学会主席,他至今仍活跃于学会的各项活动中。拉尔夫还创建了国际技术分析师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chnical Analysts,IFTA),并担任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目前在全世界拥有4,000多位会员。作为一名投资教育家,阿卡姆波拉还积极参与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SIFMA)每年一度的沃顿研究会。 阿卡姆波拉是证券行业协会理事会(Board of the Security Industry Institute,BSII)理事,目前正在参与证券交易商协会大学(Securities Traders Association University,STAU)的筹建工作。阿卡姆波拉是CMT考试教材的作者之一,并著有《第四代超级市场,从现在到2011年:怎样以前三次牛市解释现在并预测未来》(The Fourth MegaMarket, Now Through 2011 : How Three Earlier Bull Markets Explain the Present and Predict the Future)一书。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第一章拉尔夫·阿卡姆波拉(Ralph JAcampora) 您对技术分析的兴趣源于什么? 在一家天主教研究机构待了几年之后,我于1960年进入华尔街。我的本科教育背景是历史和政治学,并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所以说,我在投资这个专业上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背景。在经过一次脊髓融解手术之后,我放弃了神学研究。我父亲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威廉·道恩(William Downe),他不仅是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专家,还有自己的公司Spear Leads & Kellogg。他的兄弟比尔·道恩(Bill Downe)给我做的背部手术非常成功。道恩先生每天都要来医院看望我。威廉·道恩曾在《华尔街日报》、《福布斯》、《拜伦》(Barons)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我打着石膏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三个月,那时的我就像一只弓着背的小乌龟。道恩会把在床上看的所有读物都扔给我,于是,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和华尔街有关的东西。 医生拆除石膏夹板之后,我对道恩说,我不想回天主教研究会了。他问我打算怎么打发以后的时光。我告诉道恩,我对他介绍给我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不过是研究”,他说。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的研究还处于最早的创始阶段。 道恩先生把我介绍给史密斯·巴内公司的比尔·格兰特(Bill Grant),这家公司也许是最早开展现代基本面研究的证券经纪公司之一。格兰特建议我去弄个MBA学位,毕业之后,他再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但读书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那时的我已经27岁了。我可不想再回到学校。这让道恩先生很为难,因为他根本就帮不了我。我在基础面研究上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那时,我还要拄着拐杖走路,确切地说,我是在华尔街上蹒跚。于是,我就到处去应聘面试。最终,我在一家名为分销商集团(Distributors Group)的公司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共同基金公司,他们决定聘用我。我的工作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管理一个点数图(point and figure chart)数据库,我手头有2 000多份点数图;第二部分工作就是为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股票计算市盈率。于是,我开始用自己一半的生命来进行技术分析,另一半时间则花到了基本面分析上。这里的人很友善,也很神奇,他们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显然,我在技术分析方面很有天赋。 开办这家共同基金公司的人是哈罗德·施莱德(Harold X Schreder),他以前一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施莱德先生的经营非常成功,他坚持让每个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各自基金的选股。每个星期四,我们都要开会,在会上,基金经理需要绘制并讲解基金组合中每只股票的点数图。如果图中有任何疑问之处,大家就会吹口哨起哄,然后毫不客气地说:“嗨,你怎么能持有这么破烂的股票。”这是纪律,也是我对技术分析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 到了1968年,他们把我送到了纽约金融学院,这样的话,有朝一日我或许也能成为基金经理。纽约金融学院是华尔街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学习了一系列专业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的教师就是艾伦·肖。艾伦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1969年10月,我们开始共事。至于艾伦教给我多少东西,我自己都说不清。 1970年左右,艾伦打算邀请一个名叫约翰·格里雷(John Greeley)的人共进午餐,格里雷也经营了一个技术研究机构,他准备还带来一个叫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的年轻人。但艾伦没法出席午餐,于是,他就派我去招待这两个人。在午餐上,我和布鲁克斯都向对方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在技术分析领域认识谁?”我向他介绍了艾伦·肖,布鲁克斯则提到了美林证券一个叫鲍勃·法莱尔(Bob Farrell)的人。无疑,他们都是圈里的顶级人物,而这次会面也成为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MTA)成立的契机。实际上,我和布鲁克斯正是在格里雷的帮助下,才成为MTA的创始人。在那时,华尔街技术分析师的唯一聚会场所就是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研究机构,要拿到一张聆听通用汽车董事长演讲的午餐券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基本面分析师都有他们各自的聚会形式,比如说化工行业分析师协会、制药行业分析师协会、石油分析师协会,他们通过这种聚会分享观点,互通有无。但技术分析师却从不聚会,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团体。因此,我们想把华尔街的技术分析师联合起来。当然,我们还是要找最早的导师兼朋友——约翰·格里雷和艾伦·肖,征求他们的意见。鲍勃·法莱尔也能帮我们一把。我和艾伦在哈里斯·阿普海姆(Harris Upham)公司共事的时候,还认识了拉尔夫·罗特奈姆(Ralph Rotnem),他是艾伦的导师。在技术分析的历史中,埃德森·古尔德(Edson Gould)、拉尔夫·罗特奈姆、肯·沃德(Ken Ward)、艾德蒙德·塔贝尔(Edmund Tabell)、托尼·塔贝尔(Tony Tabell)和约翰·舒尔茨(John Schultz),他们绝对是鼻祖级的人物。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MTA的宗旨和目标都是向我们自己和公众宣传技术分析的真正价值。人们普遍认为,MTA创建于1973年。实际上,早在1970年,MTA就已经正式成立,只不过是在1973年才成为法人机构。我们的第一位总裁就是美林证券的鲍勃·法莱尔。艾伦·肖是我们的第二任总裁。这些人在圈内都属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超级名人。最终,我自己也走上了纽约金融学院的讲台,而且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哪个失误给您的教训最大? 失误带来的收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人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被过多的指标所掩埋。实际上,越简单反而越好。在最开始从事技术分析的时候,我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但却找不到那么多可以利用的指标。现在,由于计算机的普及,我们可以对一切进行检验,可以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但我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定以简单为本。我拜访过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应该说,他是查尔斯·道的活化身,我请他给年青一代技术分析师提出一点建议。他的回答是,“永远紧跟基本趋势。”假如你认识到市场上的基本趋势,那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 描述一下您的技术分析风格。 我在这个行当里已经摸爬滚打了近40年。我觉得,我做得最多、同时也可能成为我本人分析风格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史为鉴。我读大学的专业是历史学,我热爱历史。我最成功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然后,我用历史事件来解释当下市场。实际上,这就是技术分析师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研究历史。 什么样的市场状况会招致最严重的失误? 我认为,在有趋势可循的市场条件下,事情最简单。在波动更剧烈的非趋势性市场中,犯错误的几率会更高。例如,移动平均数(average moving)在趋势性市场中更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你一路前行,而不会走弯路。但是,在非趋势性市场中,绝对不要依赖移动平均值,或者至少应该慎用,因为它会让你顾此失彼。但是,一旦你识别了非趋势性市场,你就会发现,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比如说,你不会大量使用移动平均值。至于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或是不使用自己的指标呢?我的答案也仅仅是经验之谈,这么多年的历练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 您喜欢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自己的工作体会呢? 我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我喜欢分享自己的一切。 既然您采用的所有价格形态、指标和策略都已经为市场所知,那么,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工具,又怎样解释您取得的非凡成就呢?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成功有多非凡,不过,有一点我不否认,我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奋斗了很多年,所以说,我肯定还是在某些方面走对了。在投资(或是交易)中,你必须忠实于自己,你一定要灵活机动。虽然我们都要犯错误,但绝对不能一错再错。在技术分析领域,虽然我们可以马上纠正错误,但首先你要有能力、有胆量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错误,这本身就值得尊敬。在技术分析实务中,你一定要随机应变,因为你经常会发现,屡试不爽的方法可能会突然失灵。如果你不够灵活,无异于自我毁灭。我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有疑问,那也肯定出在价格身上。有些人经常会替自己辩解:“我看的是成交量”,或者“我的指标是买入售出比”。但是,你能看到的不可能是成交量,也不可能是买入售出比,只能是价格!只有价格才是永恒的标准。如果趋势看涨,即使成交量上涨幅度不大,我也会做出上涨预测。如果趋势下挫,我的预测也是下挫。我只看价格。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做。 您如何处理早期信号鉴别和提高随机噪声敏感度之间的权衡问题呢?首先,假如你是短期交易者,我指的是日交易者(day trader)或仅持有几周时间的交易者——我当然不属于这类人,你就更有可能看到随机噪声带来的干扰。在我工作过的所有公司里(我曾为三家大型经纪公司工作过),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我们保持12到18周的持股范围,其实,这正是基本面分析师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不在乎不起眼的波动。但是作为投资者,我还是要关注市场回报的,因此,异常的市场动态还是会让我们提高警惕,因为它们有可能歪曲市场的本来面目。但很多市场噪声还是可以消除的;它们不应该破坏或干扰我们对长期动态的把握。我根本就不做短期交易。即使必须要做短期交易,而且能做,我也不愿意去做,因为一定要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应对这些噪声。市场上的噪声是无处不在的。这也是我们通过止损(stop loss)措施保护自己的原因。|!---page split---| 技术分析在单独使用还是与基本面分析并用时更有效?如果我负责投资组合或共同基金的话,我一般都会从基本面分析开始。如果要让我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就一定要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是在选择买进时机和买进方式的问题上,我就得完全依赖技术分析方法了。因此,在这类情况下,我还是喜欢两者并用。但是,一旦你走进我的图表室征求我意见的话,那就是100%的技术面问题了。我们在撰写行情报告时,实际上是在撰写技术性行情报告。除技术性因素之外,任何其他外力都不能主宰技术行情报告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向投资群体、尤其是普通大众讲解投资行情时,我就要想方设法通过基本面分析证明自己的投资观点,因为这样有助于更轻易、更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我绝对不会说,“听着,你一定要买这只股票,现在绝对是探底了。”实际上,听众根本就不会买这个账。我可以对职业技术分析师这样说,因为他们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和理由。但是对那些不够专业的听者,就一定要注意你的措辞了。这也是技术分析最大的问题所在;问题的真谛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怎样解释自己的工作。技术分析的术语经常会把人们搞得一头雾水,因此,我从来不用那样的语言。我喜欢用“价值低估”或“价值高估”、而不是“头”和“底”这样的词语。“底部”是指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而“头”实际上就是价值高估的股票。请相信,基本面分析师肯定知道这些词汇的含义。 所以说,您的方法是纯粹的技术分析法。只有在向非专业技术型听众解释您的纯技术分析法时,您才会引用基本面分析的观点,对吧?在保德信证券的时候,我开发了一种独特的产品:首先,我们要对公司追踪的所有基本股票进行研究;然后,我会从中只挑选出被评定为“买入”级的股票。此时,我会问,“在这些从基本面上看属于买入级的股票中,通过定量评价,有多少可以评定为增持级或减持级的股票呢?”于是,我拿着这个买入级股票清单,再逐一进行定量筛选。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这份清单上有500只股票,经过基本面分析,其中的200只股票属于买入级。再经过定量分析,在这200只股票中,最终有100只被评价为可增持的股票。于是,我会以这100只股票为基础,对它们逐一进行最后的技术分析。在这100只股票中,可能有75只通过技术分析被认定为优质股票。现在,我们就需要对这些股票进行第三轮筛选。因此,我把这些经过基本面分析、定量分析和技术分析的股票称为“受三重庇护”(trice blessed)的股票。我们每月都会撰写一份这样的报告。我们还有基本面分析师为撰写股票做宣传工作。被评价为“卖出级”的股票,我们称之为“受诅咒”的股票,相应的,它们可能“受双重诅咒”(twice cursed)或“受三重诅咒”(trice cursed);也就是说,在基本面分析、定量分析和技术分析中的二或三个层面上被否定的股票。客户都喜欢这个系统,因为客户知道我们是用三重技术为他们把关。尽管我本人是技术分析师,但是在做出技术层面的投资推荐之前,还是要借助于其他两种评价标准。因此,我不仅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而且需要利用其他研究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政治或全球形势的分析是否会影响您在图表工作室里做出的决定呢?我习惯于一直开着电视。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报纸和杂志。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完全的真空里。那么,新闻是否会改变我对市场的看法呢?我认为不会,因为我对市场的观点是技术型观点。至于说影响,当然会有。因为像总统大选周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影响股市。我们曾就战争对股市的影响进行过一次全面研究。在战争爆发时,股票市场通常会上涨。人们不相信这个。他们觉得这只是历史,现在说起来都是故事,是笑谈。我认为,技术分析师可以让基本面分析师再升华一步。你需要从反面去看问题,因为在看图表时,我们肯定会去寻找它们背后的原因。一个出色的技术分析师总是在问为什么。 您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发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当做自己的杀手锏呢?我当然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我只是告诉大家我想做什么,但不会泄露我们的分析公式。这些公式属于我们的专有产品,我会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专用预测指标,而且我们可以让这些指标显得深不可测。其实,它们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自己也只是在做很基础的技术分析。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上涨好,下跌不好。说句实话,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不相信,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市场趋势。人们总是倾向于从主观角度去杜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越简单越好。 您经常使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分析工具吗? 尽可能地运用。它们绝不是什么交易工具。为了撰写市场行情报告,我可能会每月使用几次某个公式。我的工作并不依赖于计算机程序。假如计算机明天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我,还会像今天一样做我的技术分析。 请描述一下您每天的工作。 我每天早晨7点左右进办公室,下午6点下班。我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近。上班之前,我会看完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和早间电视新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为当天的工作找到一点感觉。所以,等走进写字楼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今天的市场会发生什么了。一切都不会逃脱我的眼睛。但问题是,在走进电梯时,我会和一些熟人聊上几句;等我走出电梯时,我就完全糊涂了,因为我必须应对真实的世界。大堂对面就是会议室,每天7:30,我们都会在那里听取基本面分析师的意见。他们会谈及各个行业,我在一边做笔记。虽然我当时会接受基本面分析师的所有结论,不过,一旦走进我们的图表室,关上门,我就会把基本面分析师的话全部抛在一边。我只忠实于自己的图表。不管分析师怎么说,我都不会买进我认为可能会下跌的股票。 此外,我还经常与客户进行谈论,并记录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每个星期一,我都要撰写大量的材料,进行2到3个电话会议,所以说,星期一是一周工作中最繁忙的一天。当然,交易商也会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电话只有一个主题:图表分析。其他两位技术分析师也要经常谈论技术指标和市场反应等问题。通过讨论,随时提出新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的房间也会像图书馆一样鸦雀无声,因为我们是在研究部,我们需要时间去思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