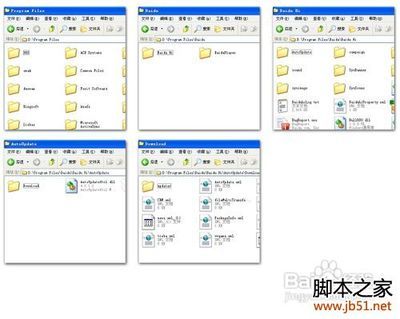我疑心,他可能更喜欢一些不那么爱看书的孩子,他们打雪仗,玩足球,现在可能是玩电脑游戏,这帮孩子可能像西蒙一样敏感,也可能懵懂无知,他们的确在麦田里四处游荡,但是,你丫千万别想再当个守望者了,你根本操不起那个心起不了那个急。
苗炜 去年1月,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去世,91岁。他说过,当我死的时候,可能好多人会说,他不是早就死了吗。今年1月,塞林格去世,91岁。其实我一直等着他死去的消息,这样就能给他写讣告了。据说很多报纸都是提早写好各色人等的讣告,但这样的文章一般都不好看,必须是死讯传来,立刻动笔,这样才更有神韵。仿佛能抓住逝者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缕魂魄。当然,塞林格隐居多年,跟呆在坟墓里没什么区别,难道他真的想活到140岁?那时候我就90岁了,我真不明白这世间有什么可留恋的,让老丫的这么起劲地活着,还搞什么顺势养生。他就没有不耐烦吗? 也许他真有什么好写的?每天上午写上那么几段,然后神秘地藏在保险柜里?也许有许多文学经纪人等着他嗝儿屁了,盘算着怎么把保险柜打开,拿他的那些东西卖钱。但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期待他还能写出什么来,那些破手稿搞得和纳博科夫那样,反而挺无聊的。纳博科夫留下那些稿子,又告诉后人把它烧掉,塞林格写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可以把其他的东西都烧掉。 在我看来,他不是那个出了几本书然后就跑到新罕布什尔州去隐居的作家,他是那个从纽约长途汽车站登上灰狗跑到西部的少年,头上还戴着那顶破帽子。这之前和老菲必告别,她在旋转木马上转个不停。这个小姑娘要是活在世上也该80多岁了,她一定是个机灵的老太太,她一定会想念她的哥哥。让她活着吧,让她活着去想念别人吧,因为她是个理智的丫头,没有哪一种思念能把她压垮,霍尔顿要是成了个孤老头子整天想念那些死去的人,那多荒唐啊。当然,我不知道活到90岁会不会更铁石心肠?
人老了有时候会犯糊涂,估计塞林格没糊涂,没有染上老年痴呆或别的什么病。在他的故事里,那些孩子永远是天才,读了那么多书,这些年塞林格躲在克尼什镇,一定看了不少书,我不知道这些书是不是让他变得更聪明了。我看悬。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西蒙,相比霍尔顿,他太聪明了,这样的人不死才怪,不自杀才怪。可他不讨厌,看他写的信还是挺快乐的,但我真不愿意看到一个90岁老头儿忽然又冒出来说话,既然你已经沉默了那么多年,就永久沉默下去吧。当个又聋又哑的人是多幸福啊,这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依我看,外面这个世界还像以前那样操蛋,要不是更操蛋,装腔作势的傻逼比比皆是,像老萨丽那样的姑娘就算相当不错了,老斯宾塞简直是圣人,摆在人面前的还是那样的混帐命运。我相信,老塞林格不会像老斯宾塞那样买个毛毯子就高兴,也不会穿着睡衣露出衰老的胸脯,在那个小镇子上终老吧。 我估计他对外面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兴趣,但我们对他的兴趣还保留着,这个兴趣一半来自于对塞林格作品的持续阅读,一半来自对他隐藏起来的形象进行形而上的探讨,等他死球的时候这股兴趣会到达高潮。我们必须这样庸俗地传播下去,非让一帮还没有变得庸俗的孩子继续看他那本书,但我疑心,他可能更喜欢一些不那么爱看书的孩子,他们打雪仗,玩足球,现在可能是玩电脑游戏,这帮孩子可能像西蒙一样敏感,也可能懵懂无知,他们的确在麦田里四处游荡,但是,你丫千万别想再当个守望者了,你根本操不起那个心起不了那个急。就看着旋转的菲必,看着大雨瓢泼,看着彩虹,看着阳光从乌云中透出来,看着她旋转一圈就衰老一分。最终,在他死后,也许会有一块墓碑标志他埋葬的地点,但上面不会有墓志铭,更不会有淘气的孩子在上面写上“FUCKYOU”。我敢肯定,死讯传来之时,有好多人感叹一句,“操!”但值得欣慰的是,50年内,不会有任何一部关于霍尔顿和老菲必的傻逼电影上演。“我最讨厌电影了,你最好提都不要提。” 听到塞林格死讯的第二天,我在上海的渡口书店,十来个人聚集在一起,朗诵了《麦田》的片段,好多个姑娘,读到“他妈的”的时候都打个磕儿,她们太害羞了。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她们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