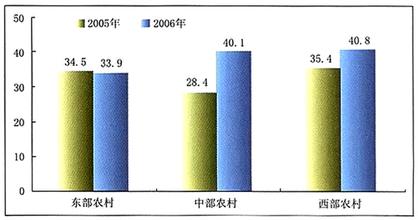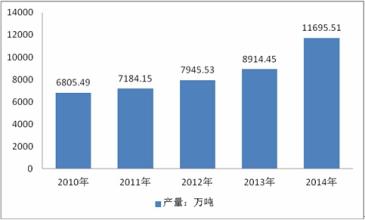同样是在北京,和燕子同龄的石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石磊来自于东北一个小城市,父母都是高中老师,家庭状况还算不错。硕士毕业以后,学中文的他进入了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年收入6万元左右。
石磊说,他从不抱怨房价,“和我没关系,反正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我不想用我的一辈子来换一套房子。”直到现在,他还住在单位附近租住的一套一居室,每月2000元,这一度被很多同学认为有些“小奢”,但他说,“我想住得好一点”。
在吃穿用度上,石磊从不奢侈,但也不会亏待自己,他有丰富的业余爱好和生活情趣,旅游、健身、聚餐,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尽管只买最便宜的票,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常符合人性”。
“我的同学很多都有房了,但是也有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贷款;很多也有车了,因为住得很远,即使开车也要每天花三四个小时上下班,而且基尼系数比我高很多,生活质量并不高。”石磊说,他并不想讨论谁过得更好,只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但多少让石磊有点感慨的是房东的儿子小强。和石磊年龄一样大的小强中专毕业,做过两天饭店服务员、卖过一阵子保险,后来都因为嫌累又赚不到钱就不做了。
“他根本不用上班,父母留给他两套房子收租金。”石磊说,其实房东夫妻算不得什么有钱人,都是普通工人,只是计划经济时代各自分过一套房子,后来又在房价低的时候给儿子买过一套大房子结婚用。现在两人都退休了,就搬到远郊区的房山去住,城里的房子用来出租。
“你想一想,我即使这辈子再努力的工作赚钱,我还是追不上房东的儿子,我们俩从出生由于房子产生的贫富差距,几乎是我一辈子都填不平的。”石磊说,这是典型的“劳动贫困”,也就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所以,还不如随性地享受生活。”
但是,石磊在老家的父母却非常担心他,也不认同他的做法,老人总是担心儿子“娶不到媳妇、养不起儿子”。
“难道我就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石磊一点都不担心,“总有女孩不想那么辛苦地为孩子、房子奋斗一辈子,也肯定有不想嫁一个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的大款。至于孩子,让有钱人去生吧。”石磊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上一代人很渴望富有、渴望出人头地,所以他们买房子、买车子、比孩子,我从不否认他们的方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燕子的第二次困惑
去年12月7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约为8.3,而2008年的中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3——而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
大城市的收入房价比更是高的惊人,广州、杭州、大连等城市均已超过10,北京、上海等已超过15,甚至20。而即使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之前,美国纽约、旧金山这种美国房价最不可承受的城市,房价收入比也不过6.5左右,甚至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
石磊依然快乐着,而现在摆在燕子面前的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第一,用手里的30万做首付,买一套他们买得起的房子,哪怕只有50平米,哪怕在五环外。然后,每个月还给银行5000块钱,不能生病、不能失业;第二,用手里的30万再买一辆车,尽管会更辛苦,但是这样他们的收入又可以翻一番。
但问题的关键是,北京的房价还会不会再涨一倍呢?
逃离“北上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 河南报道
今年春节,“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各大论坛也在狂发帖子感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开始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撤离,社会学家们则提出“回归or失败”的新命题。
在“回归”或者说“逃离”的人群中,今年33岁的周广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于1995年求学北京,1999年南下东莞和广州淘金,2002年在上海南汇创办电脑维修店,2008年底又杀回了老家郑州,整整十五年,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逃离“北上广”最经典的撤退路线。
“去北京才算进城读书”
谈到15年里的“纵横驰骋”,周广会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壮举”,“我可是最早的农民工二代。”
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父亲1980年代中期辞去乡里民办教师的职务,开始在开封、郑州打工,周广会的初、高中全是在郑州完成的。
周广会小时候在亲戚间的外号叫“小精豆”,意思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有主见。最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郑州读大专,却硬要去上北京一家民办高校。
他说:“当时就是憋了一口气,在郑州读书的时候,自己以为进城里读书了,但在同学眼中还是农村人,所以一定要去北京,去首都,就是想赌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哥哥那样呆在农村,第一,在城里住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每年寒暑假回到家连厕所都不适应了;第二对地里的活儿一窍不通,有次回家帮忙收麦被我妈骂的半死,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会干了。”周广会回忆起来非常感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这样定义“农民工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广州天河城的迷茫日子
“北京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好地方,我现在还怀念北京那种自由的气息。”提起北京,周广会不由故意加点“儿话”音,“4月份沙滩(儿)那里最美,10月钓鱼台(儿)外边的银杏树拍照可比国外美。”
每当回忆起北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和那种散落在各处的美景,他很兴奋,“但不是说你有能力就可以混在京城,北京有能力的人太多,每年名牌大学毕业的遍地都是。”
于是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线:南下东莞,到一家电子厂打工。

1999年对于学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黄金时代,虽然只是民营高校毕业的学生,但凭着过硬的硬件技术和“北京来的”头衔,他在东莞干得很不错,半年就成了业务经理。一年后,他转往广州的天河城,职业是卖电脑。
“我当时最高一个月可以赚五千,和那些名校毕业生一样。但工作无趣枯燥,一听到客户那些最简单问题,就烦得想死……”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除了解决客户问题就是上网聊天泡论坛,“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担任三个版的版主,在网上有7个‘老婆’,外号周小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