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眼看世相
劫后余生的文坛泰斗巴金,晚年用全部人生经验倾心创作《随想录》,发出“要说真话”的呐喊。当时不明世事,热衷于风花雪月作品的我觉得巴老的呐喊有点可笑,笑他年老力衰,江郎才尽,再也创作不出《家》《春》《秋》这样的“激流三部曲”来,无所事事,所以说一些废话。 随着知识阅历的增长,我渐渐地觉得自己的荒唐可笑,渐渐地悟出家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与巴老所讲的话虽相同,但是其层次却有很大的差异,一是说话的对象不同,二是两者的难易程度不同。父母劝导的是孩子,老师劝导的是学生,是未成年人,懵懂无知或智识尚浅;而巴老所要求“要讲真话”的是成年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年人,他们多是“人精”,洞明世事。 因为巴老所说的真话往往与真理与真相密不可分,“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说真话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不存在风险性的真话,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巴老倡导所说的“真话”应该是有风险性的真话,这才是其价值所在。 有价值的真话,往往会触及一些人的痛处,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真理往往被人拼命抵毁或绞杀,真相往往被人拼命颠倒或掩盖。 西方中世纪的布鲁诺被烧死,明朝方孝儒被灭十族,无不让人胆寒说有价值的真话昂贵的代价。因此林贤治在《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一文中说:“在正常社会中,讲真话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警察国家里则首先是一个勇气问题。”但是在专制的社会里,有勇气者是非常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的俊杰们往往会保持沉默,让有价值的真话烂在肚子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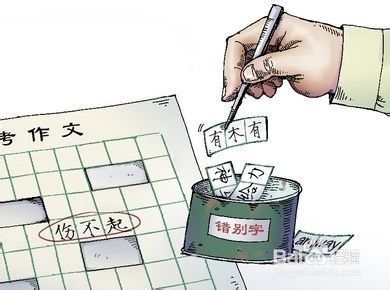
讲真话,是我们今天所大力提倡的,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但是过去对说真话打压的恶劣影响并没有消除,人们还心有余悸,担心又中“引蛇出洞”的局;而且在一些人位高权重的骨子里一点没有改变,这些人会大声地对别人说要讲真话,而自己却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自己的谎话。还有一些人明里暗里挤压“说真话”的生存空间。现在的人也受此恶习的影响,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却是从说真话蜕变到说谎话,从率真走向虚伪的过程。这是多么可怕呀,由此可见,巴老提倡“要说真话”是有先见之明的。 “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是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的感言。“要说真话”是巴老劫后余生自心底发出的呼唤。可见“说真话”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性,正如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说真话是一个社会的希望,民族的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时候才形成说真话之风呢?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