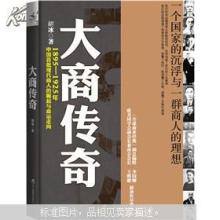赋税太重,也是申新搁浅的重要原因。此外,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而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 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的资金链断了! 风闻申新出事,各路债主纷纷上门。在债主逼得最厉害的时候,陈光甫、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二人在荣公馆陪荣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当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还有点力量。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求援。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求援,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 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求救,得到的回话是:“有物可商量。” 荣德生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次日凌晨4点赶火车去上海。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荣老大过去举债经营,全力扩张,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关键时刻说话可以算数。

从1934年6月起,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顺势接管申新。 荣宗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宗敬。荣告诉他:“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 此时,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申新侥幸逃过了被政府吞没的厄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 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 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宋曾当面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转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找陈光甫,说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当时陈光甫不在,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非常痛苦,简直就要哭了。这天会前宋子文找陈光甫谈过一次,按宋的计划,上海储蓄银行每年吃五六十万的亏。陈当面不好反对,回来与李芸侯商量后,开会时就称病在家,让李出席。 在会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陈光甫这一举动,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确实有帮助老友的情分在内,正是他的临阵倒戈,让宋子文的野心最终没能得逞。 这是荣家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荣氏集团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惜,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响了! 苦撑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上海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但荣宗敬和荣德生二人仍然决定固守。荣家只有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迁往了内地。 荣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难尽,也许因为以往的经验,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到日俄争霸东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北伐,荣氏集团总是善于因势利导,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但令荣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留守让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留在上海的荣宗敬为求自保,于1937年底加入了名为“上海市民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带有伪政府的性质。几天后,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顾馨一家的天井被人投入了一颗手榴弹。荣宗敬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小。 1938年1月4日,荣宗敬负气离开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在香港去世,终年65岁。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 荣宗敬是荣氏集团的灵魂,他的病逝标志着这个民间最大财团开始由盛转衰。 世态炎凉,荣宗敬过世的消息传到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再次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之方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 1938年5月,荣德生抱病来到上海租界。他到总公司办公,想起哥哥在世时的一切,不觉黯然神伤。他与银团达成共识,将申新每月盈余分为三成,一成还银团,一成还诉讼和解的各钱庄欠款,一成还无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维持总公司开支。 在上海,荣德生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等待时局好转。 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其子尔仁代往,说明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了,何况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威胁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依旧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荣氏集团再受重创。 乱世多变,谁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祸。1942年申新仓库启封时,恰遇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000万元只要1000万元。对荣家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翻身机会。深谙资本操作的荣氏集团,乘机抛出陈货,还清所有债务,企业完全回到荣家手里。荣德生大为喜悦,特意写道:“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终于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和“福五”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主持内迁厂务的正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 李国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亲扶养长大。1915年,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后,就在煤矿和铁路上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28岁的李国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9年冬,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李国伟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全家迁至汉口,开始负责“福五”“申四”的筹建,逐渐成为荣氏集团内核心人员之一。 1942年,国民政府对内迁的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为此,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 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操纵原料市场。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帐,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厂从1939-1945年的暗账盈利为934万元,盈利率高达161%,而明账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据1945年的账面统计,“申四”、“福五”系统共积储外折汇合美金达300多万元。 留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荣宗敬去世后,荣氏财团事实上一分为三:大房、二房以及李国伟所管的厂子,逐渐各成系统。 抗战后期,年事已高的荣德生有意淡出申新总公司管理,转而满怀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这些计划不吸收大房系投资,由二房系专营。无奈战乱频仍,好梦难以成真。午夜梦回,他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回来了,但荣氏集团似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 1946年,黑社会匪帮绑架了荣德生,把他在黑屋子里关了33天,荣家送出50万美元赎金后才被释放。人虽获释,但国民政府碍于面子,坚持追查。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备司令部只发还荣家13万美元给,其余钱款均被军警占用,而且此后数次索要酬谢。荣尔仁非常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 对这件绑架案,荣德生的说法是:“实则起意者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余为心存厚道起见,不肯发人阴私。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1948年9月,蒋经国上海打虎,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辩护,但要想救人关键还是靠行贿。因为通货膨胀,受贿的官员不要纸币,只要棉布、棉纱、面粉栈单和房子。荣鸿元关押77天,幕后交易就进行了70多个晚上,前后花费折合50万美元。 这些事让荣氏家族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失去信心。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但荣德生坚持留在内地。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也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1948年下半年,无锡申新三厂部分机器正准备拆迁台湾,荣德生一听说,就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搬回来。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考察。无锡易手前后,他每天乘包车在街上露面,表示自己还在无锡。 荣德生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从未出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开亲手开创的事业;三是绑票的伤痕尤在;四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战后的一些措施不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德生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由于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荣毅仁决定与父亲一起留在大陆。正是这一举动赢得中共对荣家的极大欣赏与尊重,那些出去后又转回来的人,与他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会后,陈毅带着家人公开到荣家做客,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件事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此时的荣德生,则在老家安度晚年。他平时“上身穿着白粗布的小褂,下面是灰士林布裤子,扎着裤脚管,一双布鞋,精神很好”。他的房间里,是“从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报纸包着的旧书”。那年他已75岁,非常关注他一手创立的江南大学的命运。 他一生都极为简朴,正如无锡梅园诵豳堂那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一生知己是梅花。梅花中,荣德生最喜欢“骨里红”。1952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热衷风水的他亲自选的,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周围种了他喜爱的梅花。 至此,荣氏家族创业一代,完美谢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