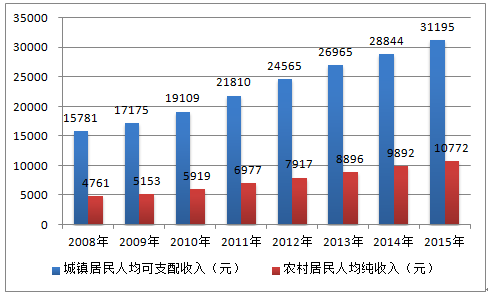而投机的存在滋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野鸡”开发商,他们从村里买到土地后化整为零转手给大批小业主建起非法住宅区。据不完全统计,此类大大小小“非法住宅区”在深圳超过500个,这让违建市场愈演愈烈并且异常复杂。
“深圳的违建是历史形成的,即使当时先知先觉,也没有人能解决那些问题。”谢志岿认为,如果没有违法建筑深圳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违建降低了当时城市化的成本。但是不可否认,深圳的城市化是粗糙的低水平城市化。 “弱势政府”困境 当时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为城市化过程中违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政府在城市化整个过程中采取严厉的措施预防制止城中村的产生,深圳的违建不会演变到今天失控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深圳扮演了全国少有的弱势政府的角色。 今天深圳市政府也承认,违建的存在,政府有过错在先:1992年深圳宣布特区内实现城市化,一些产权应该收归国有的土地,实际上却还给了原住民和原村集体经济,这样名义上城市化了的深圳,在土地和房屋产权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城市化的问题,留下了一大笔历史的欠账。 实际上政府的软弱在1989年的第一轮抢建潮中已经暴露无遗。当时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造成了原住民的心理恐慌,引发了第一轮占地建房热潮。在原住民不愿意放弃旧村土地之时,政府又在政策上作出了无原则的让步,终止了旧村改造,并撤销了旧村改造办公室。这是政府与原住民在城中村问题博弈上的第一次失败。 自1999年开始,深圳开始了立法查违建的历程。《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于1999年3月5日颁布实施后,虽然明确规定此日期以后所建的违法建筑一律查处,但抢搭“末班车”的心理促使原住民再度疯狂抢建。1999年至2002年,几部法规出台实施以来,深圳全市增加了约10余万栋新的违法私房及大量的违法厂房,违法建筑总量增加了近一倍。2004年,深圳再次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不可避免的再次引起抢建风潮,政府实际上是一再让步。 根据2002年深圳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对1999年3月5日前建的大部分违法建筑申报登记、接受罚款、补交地价款等手续后给予合法身份,最重的罚款是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元,最多的地价补缴款是当时市场地价的25%。 而2009年6月2日正式实施的《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印证了抢建的聪明所在,政府再一次作出让步,确认产权的范围不仅扩大到1999年以后抢建的私房,而且扩大到私房以外的所有违法建筑。上述决定规定只接受2009年6月2日前建成的房屋登记,此后的违建一律查处,但是抢建的剧目与以往一样并无二致地上演。 “时至今日,宝龙(宝安区、龙岗区)两区的原有集体用地和非法买卖地块,已经基本抢建完毕,特区内外再难找到大块的未建地块,城市规划和建设因为违建而更改的情况司空见惯。所有敢于面对真相的人,都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并承认,持续多年的查违政策失败已成定局,‘零抢建’更是荒谬的空话。”在查违一线的街道办事处工作多年的吕良(化名)说。 西西弗斯式悲剧之源 深圳陷入了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治理灾难。 违建查处的失败,让街道办事处承受了最为尖锐的指责,深圳网民“窝深居士”在网络问政平台上直言“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应该是基层街道管理职能的缺失”。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尤其是在深圳赋予基层综合执法职能之后,看起来无比强大的街道办事处为什么会在违建面前全面溃败?一自许知情的人士向《法人》记者透露——利益关系使然,街道与违建者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2009年年底宝安大浪街道执法队一名协管员为违建“护航”,收受22万元贿款,被宝安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该案揭开了街道办在查违工作中腐败的一角。
查违不力与执法者的腐败有着必然联系,但是如果将查处失败归结于上述腐败,不但对那些在查违路上疲于奔命的执法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会让对深圳还抱有希望的人走入一个绝望和愤怒的深渊,阻挡人们深入的理性思考,掩盖问题的症结所在。 2010年4月19日,龙岗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对龙城街道查违工作不力的4名干部做出免职决定,街道一、二把手同时下课。而就在两年前,该区龙岗街道的正处级街道办主任和两名副处级的街道干部亦是因查违不力被即刻免职。对于深圳查违的失败我们只能否认它的结果,但是不应该否认它的决心。 吕良认为,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乱是失控的本质原因。“从表面上看,街道综合执法职能强大,应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依靠一个不伦不类、单打独斗的‘查违办’来遏制和治理这一历史痼疾,实非良策。” 首先,街道办责任和职权难以匹配。在财政体制等改革的同时,街道基层的责任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不少责任都是一票否决,而相关的配套和职权却在体制创新中得到严重削弱,最为关键的就是土地、建筑审批权的收回大大降低了执法效率。 其次,职能体系零散分割。查违工作需要规划、公安、城管、交警、卫生、消防、供水、供电等多部门的配合,但是没有一个是由街道领导、指挥和考核的,特别是在考核、奖惩和任免方面,街道没有任何主动权和发言权,这导致街道在统筹功能往往难以到位而流于形式,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和整合力度。 第三,综合执法体制亟待理顺。街道综合执法的困难程度,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暴力抗法、胡搅蛮缠等情况司空见惯,执法人员的安全和信念受到很大的威胁,在很多街道,综合执法遇到的困境,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公安机关职能的配合和到位,对综合执法工作的保障作用极其巨大,但目前在这方面的职能协同等问题很多,也相当迫切需要解决。 三年前的一次综合执法经历让吕良至今印象深刻。2007年,他所在的区曾组织相关单位几百人在一条街道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大行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在场的多个部门几十号人马,竟各自作壁上观。 绝境求生
30年来,深圳的目标定位时有调整,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定位始终没有改变过,而建设国际化城市必须以统一规划为前提,失控的违章建筑像一个无底的黑洞正将深圳引入窒息的深渊。 吕良指出,对于城市规划混乱、建设高度饱和的深圳来说,改造‘四旧’(旧城、旧村、旧工业区、旧厂房)和保卫生态线,几乎就是未来这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最后希望。特别是对特区外,应当有足够的气魄和力度,进行规划、改造和建设,否则,深圳将失去城市建设和发展最为宝贵的最后机会。 在《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出台半年后,《深圳城市更新办法》出台,这部国内首部系统、全面规范城市更新活动的规章,被视为深圳的第二次革命。 与此前屡屡受挫的旧城改造相比,《办法》有三大突破:一是明确原权利人可作为更新改造实施主体,改造项目无需由“发展商”实施,同时政府鼓励权利人自行改造;二是突破更新改造土地必须“招、拍、挂”出让的政策限制,规定权利人自行改造的项目可协议出让土地;三是旧城改造不只采取拆除重建一种方式,还提出了综合整治和功能改变共三类改造模式。 所有这些突破只为一个目标,最小化改造的阻力,最大化改造的效果。但是城市更新之前依然要解决违章建筑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城市更新将寸步难行。 是否给予这些违章建筑合法身份?这是深圳至今不敢明确答复的两难问题。这些满目的违建既是深圳的希望所在,也是绝望所在。在房价飞涨的深圳,它可以实现中低收入家庭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但是这种实现的方式却须一种盗窃行为,因为他们无偿的享用着公共配套资源和社会福利。 “任何时候,政府的尊严和光荣,都与它的经验、责任、良知、勇气、创造和理想紧密相连。当前的深圳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我革新和自我超越的严峻挑战和宝贵机遇。”吕良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