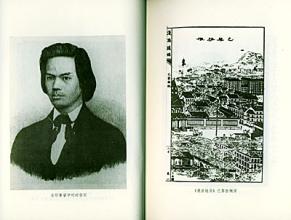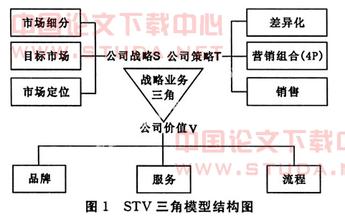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是这些?它们作为普世价值是不是够了?难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价值资源可以不是普世价值?仁爱、民本、同情、礼让、和谐、修养,对于其他地区的生命共同体就不是价值资源?
不妨将这些价值放在一起来作具体讨论。自由固然是一种价值,但它跟平等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我要个人的自由时往往会损坏平等,美国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共和党上台就要强调自由,放松市场管制,结果富人得了很多好处,贫富差距加大,民主党上台时发现自由过度,社会公共问题,缺口很大很多,于是着手解决平等的问题这样往往会高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自由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两个价值本身往往不能自洽,突出平等的时候往往伤害自由,突出自由的时候往往伤害平等。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涉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诺齐克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发现,南方的军队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同仇敌忾地抵抗北方。
刘涛:《乱世佳人》就是写这个。
黄万盛:诺齐克找到了这些审讯南方黑人俘虏的记录。法官问,“我们是去解放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和奴隶主联合起来抵抗?”那些黑奴说,“谁要你们来解放,你们将我们解放了,给了我自由,但我们去哪里吃饭。你解放了我,就再没有人对我负责了。”
诺齐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有没有选择做奴隶的自由?这是个深刻的问题。这是由自由内在的不完整造成的。通常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力威胁的选择,你是自由的,意味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你的目标,你的领袖。可是,如果他选择的是放弃自由,你能不能接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才说,自由背后有更深刻的问题,即责任。当你追求自由的时候,你对自由所负的责任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许愿,不是一个空洞的权利,自由是一种生活,一种需要负责任的生活。
刘涛:我觉得孔子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黑格尔亦区分: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胡来不是在自由王国,而是在自然王国。
黄万盛:只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还不够,还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才是最精彩的。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长期的培养和修炼。孔子把自由看作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生命历程无止境的追寻和成全,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大智慧。前面提到的诺齐克的困惑,在孔子这里就不存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之所以如此看重正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平等还不是最深刻的问题,平等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东西,公正应当是更深刻的价值。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即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人与人沟通应该存在一个理性原则,他是在反思和发展启蒙以来的这些价值。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重要资源可以参与建设。比如北宋大儒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比如“推己及人”,比如“诚”,比如“信”,交往的形上学、存有论、功夫论等,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关怀重点,这些深刻资源为什么不能参与西方价值的改造建设呢?
刘涛:那么民主的价值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黄万盛:民主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价值,但西方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很多教训,不仅要吸取其经验,也要吸取其教训,才能实现制度创新。
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建设公共理性比一人一票更为重要。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的偏执的人,该怎么办?怎么能从政治哲学上说明多数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历史上由多数造成的灾难比比皆是。可是民主必须是多数决定,所以这其中有一些深刻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才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提出来。
公共理性只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话语,怎样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这是个问题。阿玛提亚·森基于印度的经验,提出另外一个词叫 Public Reasoning,即是公共伦理,将其变成一个动态过程。国家的重大决策一定是各利益集团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论辩,这样就将民主从选举机制转变为管理机制。
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强势的价值,在遇到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社会,到资讯社会的历史变革的时候,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黄万盛: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了解这些价值的发生和变化,更应该了解中国的资源能够做什么,这才是我们主要的任务。
刘涛:我们刚才讨论了西方的强势资源,您觉得中国的“文化资本”中哪些比较值得注意?
黄万盛: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而且从价值结构来说也更完善,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这叫做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是:安全、公益、信赖和学习。
第一是安全。天道人心,体恤苍生,以民为本。人民有免于贫困、免于战争、免于迫害、免于恐惧的权利。安全是民本的最大要务。安是安身立命,不是动物性的存在,是真正知道自己怎么生活。
第二是公益。公益比公义要大,公义主要是精神原则,但公益是转化为社会现实和社会福祉。要做到公益社会,不发展信赖是不可能的,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发展宽广的同情。
第三是信赖。从诚道可以推出信赖,从信赖可以发展连续的社群意识,由此而及大同。我讲的信赖是在公益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所谓天道无欺,一视同仁。
第四就是学习。不通过学习,永远达不到目标。一个人活着若知道要学习,这个人的暴戾之气会减少,往大说战争亦会减少。学习才是和平的保障。美国现在的傲慢是因为他们完全成了教导的文明,他们自认为拥有最好的制度,故要将民主等送到世界的四面八方。
有西方学者曾经问我,中国不是宗教传统的国家,它的精神世界是怎么维持的?社会生活准则靠什么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不是把终极关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它的终极关怀不是可以感性化的天堂,不是生前赎罪、死后兑现,不是末日审判、成圣或成魔。中国智慧中的终极关怀是一个信念、一种向度,它坚定地相信人具有无限完善的光明前景,人可以在现实生命中不断超升。而这种信念的达成,这种完善和超升的通途,就是学习。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开放体系。所以《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快乐的人生。
知识分子的使命
黄万盛:一个国家形象的建立不仅仅靠财富,还要靠其背后的价值。很多小的国家事实上是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比如基督教的经验是在耶路撒冷发展出来的,那是多么小的地区。
所以孔子重视文化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暴力来维持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如果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那一定是短命的。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主要就是靠税收、军队和警察。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有突破,他的交往理性看到对话、聊天、茶馆、圆桌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意义,这就接触到文化资本的运作了。
刘涛:士是四民之首。我想近代很多知识分子慨然以士自任,自觉去“弘道”,这从近现代中国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黄万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就是要参与其中,使得这个政治系统符合天道人心。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这是自觉的体制外的批评意识。所以,我说西方是批判的建设性,中国是参与的建设性,两者不同。
和谐社会,重要的就是参与。中国名留青史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因为抗议精神,但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的不单纯只是抗议精神,亦有合作、参与,为民请命就不能只用抗议精神来理解。
中国知识分子志在“君王师”,要教育君使之合乎天道,其责任比君还要大。所以他们的参与不是空洞的,一是教育和培养,二是辅佐,三是批评,四是抗议。如果这个朝廷真是无药可救了,知识分子可以跑到民间,成为抗议的领袖。所以知识分子是在庙堂和江湖之间。这个参与是既参与社会,又参与政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转变社会当做政治目标,而不是将政治利益当成最高的目标。
西方的批评传统当然有价值,对政治可能的作奸犯科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政治的腐化。但其问题在于,他们不能将政治的有价值的方面凸显出来,只是强调了政治的阴暗方面。法国当年甚至有这么极端的言论:“宁可跟着萨特犯一百个错误,也不跟着雷蒙·阿隆做一件正确的事。”雷蒙·阿隆是西方的异数,他参与政府政治,做文化部部长;萨特则是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热衷于游行和抗议的街头政治。
中国与此不同。我们有独特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资源被灰尘蒙蔽得太久了,我们要将其打扫出来。首先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参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然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亦会进入世界之中。我有一个信心,如果参与的建设性得以充分发挥,民主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形态,民主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这里既是学术创新,也是制度创新。这是需要有使命感的,下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或许情况会好些,至少我有这样的期待。
[本文是刘涛副教授在访问哈佛大学时与黄万盛教授的思想对谈,本刊整理并有删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