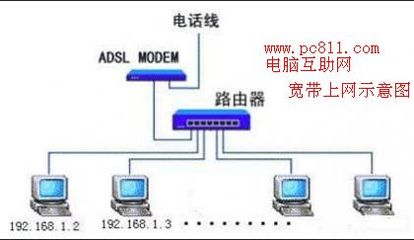和分权运动一样,选举制度改革也是新工党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工党却迟迟舍不得出手,直到这次大选前夕,才匆匆抛向自民党。另一项改革也不算成功:大规模减少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议员,通过党派提名选举授予议席,这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献金丑闻”,极大地败坏了英国政治的声誉。相比之下,新工党带来的分权运动,可能是效果最好的改革,尤其,北爱问题和平解决,苏格兰和威尔士也享受着自治带来的愉悦。但对于英格兰人特别是传统的保守党支持者来说,这种权力下放,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让英格兰成为政治受气包。在今天英国,苏格兰虽然无法彻底独立,但是他们对于英格兰的排斥和敌视,却在慢慢增长。
“大社会”的呼声
相对于自民党狭隘的政治目标而言,今天的保守党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理念“Big society”(大社会)。从政治源流来说,这个概念不新奇,英国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对于英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之一就是“organic society”(有机社会),强调了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归,而不是受制于巨大的国家机器。
在新工党后期,特别是从布莱尔第二个任期末段开始,工党逐渐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扩大,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超过400万个摄像头监控着英国6000万人口,与此同时智能身份证方案推出,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英国社会感到了一丝恐惧。“保姆国家”(nanny state)和“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心中的担忧:这个国家在用中产阶级的税收,去补贴懒汉和外来移民。原先已中产阶级化的新工党,失去了继续向英国社会阶层的中间地带(Middle England)推进扎根的动力。
最为明显的是,在2008和2009年增选中,工党开始主动攻击保守党的阶级成分。尤其是在北部克鲁威的增选中,工党在当地的工人支持者发起了类似“阶级斗争”的选举策略,结果仍然被保守党攻下了这个票仓。此事件的政治学意义很少被人谈及,但是笔者认为,新工党的理念从此走向没落,被迫重回传统的工人阶级怀抱。1997年新工党的理念是“第三条道路”,想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做一个切割,拥抱今天英国更加广泛的中产阶级。很遗憾的是,在本次大选中,新工党只能靠在北部的传统工人区和非英格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勉强阻止保守党取得多数席位。新工党即使再想拥抱中产阶级,也难以丢掉自己的选民基本盘。1997年上台至今,新工党最为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帮助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北部和中部城市成功转型,使得大量的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感到被社会抛弃。
考虑到新工党回归左翼,卡梅隆在大选最后阶段才喊出“大社会”的口号,就是个战术失误。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07年保守党年会上就已成型。家庭是大社会的核心单位,而卡梅隆当年演讲的名言就是“家庭是最好的福利”,他所提的重要对策之一,是给结婚的男女提供减税政策。在今天英国,攻击福利国家,抨击失效家庭(指父母无法抚养子女,不愿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尤其是右翼报纸拿外来移民享受英国福利来说事,俨然成为风潮。这说明民众对“大社会”有着现实需求,而在政治哲学领域,卡梅隆早已有了自己的“帝王师”菲利普·布兰德,其很多政治演讲都由这个人来起草。去年10月,布兰德已提前宣布了“大社会”的概念。很遗憾,出于谨慎,卡梅隆没有适时跟进。
是否还有新工党
在本次大选中,自民党的目标很狭隘,保守党的理念很宏大,只有工党失去了方向,只剩下布朗的保经济保权力。一本竞选宣言写下了满满的数字,新工党早已名存实亡。
“保守党的圈子,工党的帮派”,这是英国对两大党派系传统的总结。布朗辞职之后,新工党“三驾马车”只留下曼德尔森;原来的布莱尔系和布朗系即将开打新党魁争夺战,他们代表两种政治理念,胜者将成为未来工党的灵魂。布莱尔系的衣钵可能被大卫·米利班德继承,他的弟弟埃德·米利班德属于布朗一系,两人其实都偏向右派;而布朗系的继承者是埃德·鲍尔斯(Ed Balls),他是工党中社会主义思潮的捍卫者,他的太太也是工党新生代人物,曾任首席财务大臣。除了这两派之外,工党内部传统的工会势力也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前任内政大臣约翰逊。此外,前副首相哈曼女士也将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这若干派系的竞争会给工党带来类似新工党的价值观,来对抗保守党日趋成熟的“大社会”理念吗?不妨看看保守党早年的例子:1980年代保守党内部对于未来争论不休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从手提包拿出一本书,“啪”地扔在桌上,“就是他了”。众人一看,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当年,英国被工党带入福利国家,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免费医疗系统NHS,当福利国家建成,工党失去了政治思想上的原动力,是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经济拯救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将英国带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在本次大选之前,撒切尔夫人的长期政治对手、工党前党魁福特(Michael Foot)逝世。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因为福特极端左翼的政治立场,才使得撒切尔夫人的极端自由主义立场看起来也可以接受。福特的极端左翼立场,还使得一批工党资深政治家选择了脱党,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人帮”。他们在离开工党之后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然而,经历了8年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始终无法成为英国政治的主流,因为他们无法打破英国政治实际上的两党制传统。1988年,他们与当时的自由党联合,成立了现在的自由民主党。
工党在“四人帮”出走之后,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新工党诞生前,工党领袖基诺克逐步排除工会势力对工党的控制,将福特的左翼思想通过党内选举来逐渐弱化。布莱尔、布朗和曼德尔森正是继承了基诺克的遗产。这个过程进行了近10年。而这个10年,刚好是工党饱受保守党压力的时代,同期,刚好是冷战、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传统的工人运动市场消退,工党必须寻找新的市场份额,但是,只有在北部,比如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强大的工业基地保留下来的工人选民基础,才是工党生存的沃土。现在,工党似乎回到了当年那个彷徨期,还会再有基诺克那样的人引领它走出失语的困境吗?
变革如何有建设性
在今日的英国政治中,卡梅隆和克莱格都在高喊变革。他们赢得权力的结果,确实是一个变革:英国出现了自1974年以来的第一个联合政府。这也许是走向未来的开始,可惜的是,笔者认为“大社会”现在更像是一个抗议性的选举口号。布兰德的新书《红色托利主义》(Red Tory)翻下来,不妨叫做《卡梅隆同志讲话选》。布兰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大社会”的构想,在经济上没有合理论证。
回到选举。一个理想的状态,也许是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改革成功,改变政党政治生态。所谓成功,就是能够突破英国政治的地缘性,南北不再是工人子女与地主后代割据的领地,选民结构上出现一批是早期新工党和自民党的群体,一批是卡梅隆时代新保守党的群体,两者在传统的南北地区上均衡分布。但是很难说,这种选举制度改变和选民结构变化,到底谁作用谁,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命题。
除此之外,检点新工党剩下的遗产,分权运动至今顺利运行,议会改革也已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新工党在全球纵横捭阖的外交遗产却无人继承。英国传统外交中,欧洲排第一位,美国后来居上,而目前联合政府中,保守党的卡梅隆反欧,恨不得退出欧盟,自民党的克莱格反美,是坚定的伊拉克战争反对者。笔者相信他们两个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同样缺乏了解和知识。新任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是英国政坛的老兵,但他也是“未来世界”的陌生人。保守党能否再现新工党的外交辉煌,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可能走向封闭的英国,时常在笔者脑海中盘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