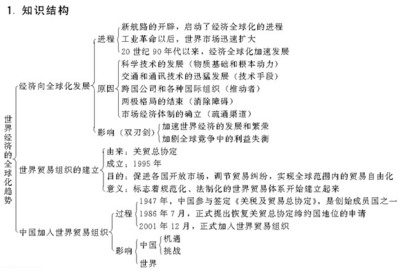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是公共财政。这样下去,真有可能会陷入有增长没发展的境况,老百姓的福利也没有改善。
文|郑景昕
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迅猛发展的秘密是什么?通常人们会将这个“秘密”定义为“中国模式”,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却向《英才》记者矫正,“中国模式”会带给人一种“终极目标”的错觉,而中国的发展其实还处在向前探索之中,因此称为“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更为妥当一些。
姚洋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门类相比,发展经济学不免更着重于经济体的长期表现。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世界的竞争最终是思想的竞争。中国30年来的发展一直不忘强调“中国特色”,也正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被称为“中国经验”。姚洋认为这种“中国经验”可视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思想贡献。
但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也能适用吗?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未来会面对什么挑战?中国该往何处走?“
中国经验”的秘密
中国政府比较务实,这与我们的儒家传统有关系。中国人不重视形式,只重视结果。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快速腾飞的秘密是什么?
姚洋:在过去的30年或60年间,我们的成功经验大概有四条。
第一,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我们是经过革命的,革命把原来的那些精英阶层全给打散了。比如菲律宾经济几十年来没多大起色,上世纪60年代,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而现在,菲律宾的人均GDP才2000多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很大原因是菲律宾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控制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这些特权阶级享有祖祖辈辈世袭的特权。发展中国家有一个通病,就是存在世袭的强势集团,别人很难进去。
中国的革命不管多么血腥,它造就了一个比较平等、流动性比较大的社会,这是奠定了我们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第二,正是因为有这种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政府变得比较“中性”化(disinterested)。所谓中性是指,政府并不长期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中国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但政府自己也有利益。我们过去30年做得比较好的是把政府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我们历史上有很强的“贤能政治”传统。在潜意识里,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相信这种贤能体制的,你要是想当官,就必须有能力、有德行。
第四,中国政府比较务实,这与我们的儒家传统有关系。中国人不重视形式,只重视结果。这有坏处,如法律不严。但在转型期间,它特管用,我们搞了很多不中不西的制度,如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等。比如价格双轨制,计划经济就是短缺嘛,突然一放开价格,价格就猛涨。一物二价为我们顺利转型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英才》:这些转轨中有用却又特殊的东西固化下来,是否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姚洋:对。这就是坏的方面。但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对世界是有意义的。西方国家在推行制度的时候,实际上是不管当地的条件。《英才》:西方推行制度更注重程序?
姚洋:对,西方注重制度的纯洁性。比如推行民主,它就说,要治理腐败,要搞宪政。那具体谁去搞宪政呢?谁去治理腐败?说不清楚。最终你还要靠当地人,否则又回到了殖民时代,你得让本地人自己来建立自己的制度。这时候就会发现如何建立制度可能更重要。中国通过自己的摸索建立了自己的制度。
中国发展的挑战
我们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失衡得非常严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带来一连串的问题。
《英才》: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世界发展历史看,许多国家在这个收入水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避免?
姚洋:中国要想办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期面临的问题是:首先,这个时期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动荡;第二,经济要发生转型,以前是农民变成工人,经济就增长了,这个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再这样搞的潜力不大,要提高人的素质,很多国家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为什么不足?反过来这又与精英控制有关系,精英不关心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中国为什么有这样的危险呢?我们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失衡得非常严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使得我们的出口必须很多,出口多了发现用不了,没有足够的需求去购买国外的产品,外贸盈余又很大,外贸盈余大了之后要维持固定汇率,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大,外汇储备增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通货膨胀对老百姓又不好。进入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财富都跑到谁那去了?都跑到企业、政府手里去了。这就会出现问题。经济在快速增长的时候,老百姓收入的占比还在下降,这就是问题。
《英才》:历史上有没有避开这种陷阱的例子?
姚洋:日本也发生过这种问题,不过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日本的基尼系数很低,只有0.36左右。但它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基尼系数达到0.47,比我们现在还高一点。为什么60年代中期之后,就下降了,这是将财富投资到老百姓身上、实实在在的东西上。中国政府现在收入大概有8万亿,其中40%-50%变成了资本形成,如公共设施铁路、公路,这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没有超过8%的。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是公共财政。这样下去,真有可能会陷入有增长没发展,老百姓的福利没有改善的境况。

最终是思想竞争
不是纯粹地就孔子的思想论思想,而是如何把孔子思想运用到今天的社会治理上。这才能把孔子给激活了。
《英才》:你说世界竞争最终是思想的竞争,我们该如何融入到这场竞争中去?
姚洋:中国如何参与竞争?我觉得我们对儒家思想的挖掘不够,特别是在朱程理学之前的儒家思想发掘不够。我们现在接受的关于儒家思想多多少少都是朱程理学固定下来的东西。朱程理学纯粹地强调道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瑞。
我觉得孔子应该更加深入地挖掘,关注现实地挖掘,不是纯粹地就孔子的思想论思想,而是孔子思想如何运用到今天的社会治理上。这才能把孔子给激活了。现在我们搞的孔子学院、新儒家等其实都不够,都没有把孔子读活。读活就是要把孔子的思想用来解决今天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问题。
《英才》:孔子思想有这个实力或可能性吗?
姚洋:我们整个两千多年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孔孟的思想之上啊。
《英才》:最后我们这种思想不是被人家西方思想给击败了吗?
姚洋:不能这么说。在16世纪的时候,中国其实已有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是全球化的中心地带。
中华文明最终走入了一个所谓的“高水平陷阱”。我们高度分工、高度发达,整个农业、商业,包括当时条件下的工业都相当发达,但最后没有真正突破,我们有所谓的亚当斯密式的增长——分工加深、市场扩大,但我们没有库兹涅兹式的增长,没有这种技术的突进,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业社会。西方新兴的文明在上升——工业化。中国不是衰落了,中国是被别人赶超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