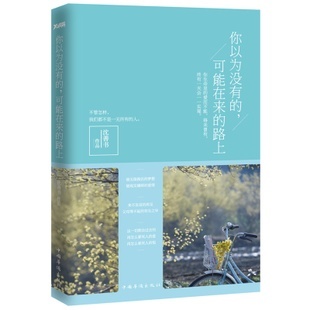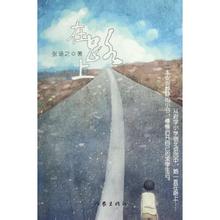空寂得让人不安,人异化成无生命的石膏像,依然紧迫,从现实里逃跑,又从历史中逃回。极不真实的景象,仿佛外来世界的文明遗迹。 长长的投影折射出一个世纪的忧惧,基里科的《预言者的报酬》看似不可理喻,却有明确的哲学表达:“一个人居住在这世界里,如同居住在一个巨大陌生的博物馆中。”将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唯一可知的,它切合了我们内心的彷徨。 时间无情的流逝,来不及思考,苟且先活着,也许,活得更纯粹些。在基里科创造的秩序井然的假象里,喧闹的广场绝无人烟,到处流淌着失落感、孤零感。颠覆我们熟悉的生活,推翻我们习惯的认知,重新审视世界,“为什么活”比“怎么活”更有价值。 人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身处何种境地,或置于怎样的未来前景?而另一种更深奥的逻辑,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重大选择面前的一筹莫展。 根据玛雅预言,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由于对未知灾难的恐惧,就此拍摄的美国大片《2012》,曾引起民众恐慌,以致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辟谣。其实就整个生命而言,未知的恐惧不是威胁,反而能深化内在精神的持续成长,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人形象的描述为: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 今年3期《英才》推出钟伟教授为本刊独家撰写的专栏文章《1000万未必够养老?》,出人意料的引发全国性大讨论。对此文钟教授当初特别附注:“我尝试用历史和数据说话,不包含任何感情,但是解剖现实政策的残忍。”很性情的他,还为自己的专栏系列取名“清水集”。其深意是:“濯足沐冠之用、是君子不朋、也是寡然无味。”

是世事难料,抑或反应过激,总之文章发表后激起千层浪,仅网上扔“板砖”的就比比皆是。于是我跟他讲笑:盖房子不愁“砖”了。他也直面:“苦笑而已,如今没人做数据和用理性了。”并借古人之言:“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这倒让我记起,他当时一并发来“供一乐”的文章《成功阶梯和人生境界》中那些细碎文字:“30岁时,应该知道自己能做成功什么了,知道天赋和勤奋,相信年轻没有失败。40岁时,应该知道自己即便足够天赋和勤奋,也有可能做不成什么,不再困惑于上天未赐机缘。50岁时,应该知道凡事定当尽人力、听天命,努力了就不会太介意结局。60岁时,对一切人生的荣誉、争议和诽谤,都左耳进去右耳出来,深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70岁时,人们就更容易理解重要的不是你成功了,也不是你的对手都失败了,而是环顾四周,你的朋友对手都死了,而你还活着。那么一切所谓的成败得失,都是恒河一沙,不妨看淡看清些。” 在史学界,有一位备受争议的学者黄仁宇。7年前还在网通任职的田溯宁颇为推崇他,并对我说:“中国为什么在明朝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完成在数字上管理国家。”而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里的一段自述令人慨叹“我开启这段生命是时,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问题在于,在过程中我逐渐卷入比生命更宽广的历史。到最后,我避免放肆时,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在此同时,我历史观点中的实用价值让我无法维持缄默。” 其实1000万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何必大惊小怪。真实的焦虑该不是财富多少,而在于内心的定力。有人问遇缘禅师:“众手淘金,谁是得者?”禅师答:“溪畔披沙徒自困,家中有宝速须还。”点破淘金淘不到真财富,真财富在我们心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