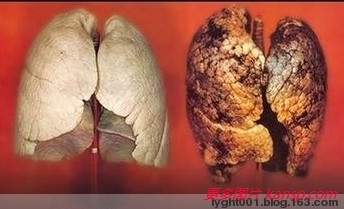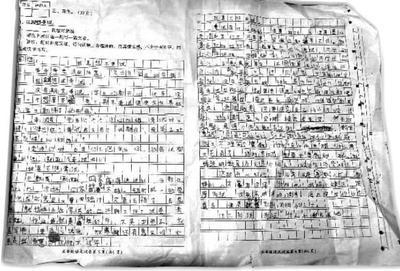我小的时候,对脏话的词汇量掌握,远胜过同龄的孩子,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她是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疯子。
外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附近的马路边,对着来往的车辆咒骂。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眼里,她只是一个奇怪的老太太,一个仿佛在路边自言自语的老太太,因为她骂街的声音不算大,而且带着方言,若不仔细去听,确实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我那时候比较小,有时候会把那些听不明白的内容挑出来问我妈。
我记得我问我妈,外婆说的“糖包子”是什么意思?
我妈说,不是“糖包子”,是“搪炮子子”,就是挨枪子的意思。
我问我妈,什么叫“狗日的”?
我妈说,这是说,这个人很讨厌,就像狗像当年侵华的日本人一样。
我又问我妈,那什么叫“骚婊子”呢?
然后我妈就发火了,她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以后这种话,一个字都不准说。
(爱华阅读配图)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骨子里勤学好问的品质,很可能就是那次被她摧毁的。虽然我妈坚持认为,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过。
外婆年轻时,家里很有钱,她是她生活那个小镇里,最富裕人家里的三小姐。外婆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人,因为我外婆读的不是乡间的私塾,而是洋学堂。
我妈说,我外婆还是小镇里第一个坐着小轿车出嫁的姑娘。我想象过这个画面,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外婆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我外婆还留着披肩的长发,坐在老式的汽车里,从完全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人群里开过。我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围观镇民充满羡慕嫉妒的议论声,江家三小姐的婚礼,注定在当地是一场最吸引眼球的盛事。
外婆清醒的时候,我和她聊过她家当年的财产,我问她:“外婆,听说你家当时开了不少家商店,什么绸缎庄、干货店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田产,是不是真的?”
外婆当时白了我一眼,然后没好气地说:“这关你什么事?”
我知道这是不关我什么事情,因为那些在解放初期就被政府充公,被贫下中农瓜分的地主阶级财产,是不可能和我再有什么关联了。
但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为自己感慨一下造化弄人。
我原本应该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公众嘴上瞧不起,心里很羡慕的富三代。
我原本还应该是一个时常会无比幽怨地思考,为那些成天纠缠我的美女们“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这样的问题而纠结、万分痛苦的高富帅。
可如今我清楚地知道,爱我的人就是爱我的人,一点悬念都没有。
我没见过我外公,对于他,我只能从家里保存的两张旧照片上分辨出他年轻时是一个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光亮的公子哥。
我妈对我外公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在我妈很小的时候,我外公便病故了。
我妈懂事的时候,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寡妇。
那一年,解放后的中国,所有人都划定了家庭成分,外婆当之无愧地被定为地主,没收了全部财产。
我妈也没有见过外婆长发披肩、高贵冷艳的样子,在她心中的外婆,只是那个在批斗会场地中间目光茫然的地主婆,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着,聆听着贫下中农代表们的教导。
在参与批斗的农民阶级兄弟疯狂的“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声中,那个人人尊敬羡慕的三小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假想敌,一个所有革命故事中蛇蝎心肠的反派。
外婆也哭过,不过不是在批斗的时候,而是粮食困难好转后,从前家里的丫鬟带着几斤猪肉从外地一路找来,两人躲在屋子对着掉眼泪。
我妈发现外婆精神异常,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外婆原本已经在省城住了几年,但国家的政策有了变化,进了城市的地主分子全部被赶回了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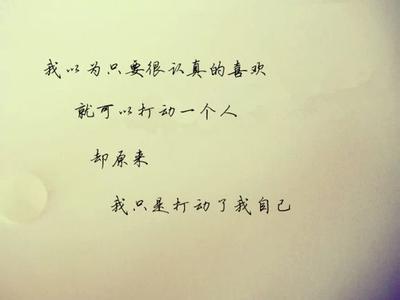
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哭了,因为她知道外婆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无疑是民怨最好的宣泄口,外婆成了一个“搪炮子子”。
有时候外婆也会进城,来看我妈和我舅,只是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我妈为外婆回乡掉眼泪的事情,被同学举报到了学校。我妈因此在年级的大会上做检讨,检讨自己和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的恶劣行径。
在学校里,我妈原本就是异类,在整个年级中,只有两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学生,我妈属于降级录取的考生,和我妈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上了名校,而我妈只能上普通的本科,我妈知道自己的录入来之不易,自然在政治上不敢走错一步。
外婆开始频繁地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妈和外婆走在街头的时候,外婆也会旁若无人地说话,就好像一直和空气中站着的一个隐身人说话一样。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外婆说:“我没做过。”
外婆说:“我没有。”
然后不停地重复再重复。
外婆那些自言自语,我也听过,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对白存在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