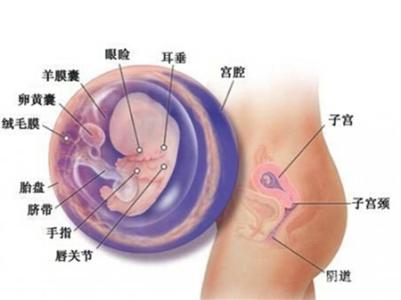我小的时候,时常看隔壁张二爷练枪。
他常用的是一杆红缨枪,白蜡的杆子,点钢的枪尖,杆头处一撮飘舞红绒,立起来比他本人还高几分。他白日里是不练的,只穿着一身泥金色的大袖马褂,左手提着鸟笼,施施然地踱着方步,往街头巷尾里溜达,十足的旧社会地主派头。他年纪不大,三十岁还不到,但邻里乡亲的见了他,大都得点头哈腰地唤一声“二爷”。
到了晚上,才是他耍枪的时候。待得回到家里,用过晚饭之后,他把院子一关,就换上了一身白绸的紧身短打。白日里的纨绔习气一扫而空,一双三白眼精光湛湛,脸上登时带着锐利的煞气,一杆大枪握在手里,仿佛活物似得,只见他扎、刺、拨、打,一招一式施展开来,月光清亮如水,照得人如猛虎,枪如蛟龙,带着猎猎风声,枪尖一点寒光吞吐,端的是气势非凡。
父亲与他交好,时常去他家里品茶。有时候相谈甚欢,就干脆留在他家里用了晚饭,我也便有幸见识了他的枪法。有一次他使得兴起,陡然大喝一声,反手转身,一枪点向院中杨柳上的一只黄莺,父亲惊呼出声,却见那黄莺扑腾腾地受惊飞起,那一枪以分毫之差,扎中了树干之上。
他哈哈大笑,回过头来,看我神色如常,便逗我道:“我要刺那鸟儿,你怎么不怕?”
我道:“你瞄准的本就是树干,又不是鸟儿,我怕什么?”
张二爷“咦”了一声,走上前来,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又抱起我前后打量了一番,冲我父亲道:“倒是没发现,这孩子眼力不差,身体也好,倒是个练枪的好苗子,你要是放心,不妨让他时常来我这看看,如何?”
父亲笑道:“你要是能收他为徒,是这孩子的福气,我还求之不得呢。”
张二爷却摇摇头:“收徒不成,你是知道的。但是如果不用师徒名分,我倒是可以传他一些武艺防身,也算一门本事。”
就这样,我开始随着张二爷学枪了。我生性好闲贪懒,练架势大多是敷衍了事,连入门的扎个马步也不认真,更毋提晨晚两课了。二爷也不在乎,有时候见我偷懒,便干脆喊我过去,把枪扔到一遍,两个人吃些糕点茶水,对坐聊起天来。
有天他问我,说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年纪轻轻,乡亲们却都尊称一声二爷?
我说不知道,但看得出来,大家都怕他的很。
他哈哈大笑,说怕是当然了,倒退二十年,他们张家可是这城外山上,落草为寇的山大王,手下上百号人,几十条火枪,甚至还搞到过一台土炮。在城里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主儿,虽说过去十多年了,但余威犹在,他小的时候,可没少祸害过这些乡亲邻里的。
我不由好奇心起,问他后来怎么从良了?
他呷了一口茶,嘿嘿一笑,跟我说起那些年的往事来。
原来他父亲当年身为一寨之主,也是个有血性的。日寇侵华的时候,打到县城外头,他宁死不降,拼了满寨的人马和日军周旋,最后寨毁人亡,连二爷的娘都死在了日军手里,只剩下他带着不到十岁的二爷,投靠了国民政府,凭借一手家传的厉害枪法,当上了军队的教头。
二爷那时候年纪虽小,却也跟着一群大人有板有眼地练起枪来。他亲眼目睹母亲惨死,矢志报仇,下的功夫比谁都勤,加上天赋使然,短短几年间,但论枪法,除了他父亲之外,整只军队里已经没人能是他的对手了。
结果还没等他年纪到了能上战场的时候,15岁那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从此再也没能有机会亲手给母亲报仇了。
又过几年,内战开始,他父亲受够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毅然带着他投靠了新四军,甚至参与了解放南京的那场渡江大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父子二人毕竟不是正规军人,便辞了军队里的职务,又回到了老家,找出了当年埋下的一些剩余的金银财宝,地契田契,置办了偌大的一份家业。没多久,他父亲因病去世,便留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倒是有不少人介绍,想给他找个女人,把家业操持起来,他却没什么兴趣,便一直就拖了下去。
之后,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开始了,二爷一腔热忱,把对日寇的仇恨转嫁到了美国人身上,第一时间报名参军,赶上了几场轰轰烈烈的大战。
“……那时候是真险啊,我们都弹尽粮绝了,对方是三个美国佬,手里拿着匕首,我就剁了一根树枝,权当枪用。那美国佬块头可大,跟一头熊似得,大吼一声,就冲我扑了上来,我抽身错步,枪尖那么一点,嘿,他那匕首就飞了出去,他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我又是一枪,当心窝子戳了过去,这一招本来是禁手,江湖恩怨,哪里用得着这么狠的?但是战场上就不一样了,那树枝头被我削尖了,一戳进去,鲜血四溅,他仰天就倒……”
二爷每每讲到那段经历的时候,都眼睛放光,手舞足蹈的,跟我比划起了他用的一招一式。我其实是不太信的,他实在讲的太玄乎,他枪法再厉害,真的就能神成这样?他也不管我信不信,总能兴高采烈地继续讲下去:
“……他拿枪指着我,让我放下武器,我就慢慢跪了下去,装作虚弱无力的样子,手偷偷摸上了地上的一截铁棍。他看不见我的表情,我却能看到他的,就在那时候,他右肩微微一动,我知道他要扣扳机开枪了。要知道我们习武之人,练到后来,就是追求的一个‘惊’字,所谓惊弓之鸟,就是你刚拿弓箭对着我,我就能感受得到,下意识地做出反应。听起来玄乎,但就是这么个道理。我电光火石之间,铁棍一扎,合身扑了上去,耳边传来枪响的声音,他却被我扎倒了,身后还有一个美国佬,拿着军刺就扑了过来,我比他更快,猛地向前一突,他还没刺上我,眼珠子就瞪了出来,被我一棍戳中了肚子,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我便当故事听,倒也精彩。每次说到最后,他都摸着自己的右腿,叹气说,要不是腿伤了,被送回来,他真想死在战场上。
我见过他的大腿,上面一个深深的枪眼,是被子弹打进去的。我见他日常行动与常人无异,甚至练枪的时候都毫无异状,便只道他恢复好了。他却说不是的,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条腿已经不中用了,若是以现在的情况和自己以前斗枪,三招之内,就能被打趴在地上,右腿使不上力气呢。
“你要记住。”他看着我,认真地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枪是百兵之王,你握着枪的时候,胸中要有一股子气。你出枪的时候,手要松,气要硬,从大腿、腰,到大臂,手肘,一起发力,才能把枪劲发出去。力的功夫做足容易,但是气的功夫要到,就难了。为什么枪要练一辈子?就是因为要练这股气。枪用的好的,没有小人。小人没那股气。”
我总是感受不到,他所谓的气究竟在哪里。他说不急,以后我慢慢就会懂了。
后来我上了学,跟他练枪的时间就更加少了。只有放假休息的时候,会跑过来跟他坐坐,聊聊最近的趣事。他年过三十之后,形容更加清癯,两鬓竟斑斑点点冒出了些白发,我有时候也劝他找个女人,省得一个人孤零零的寂寞。他说也见过几个,但是没有谈得来的,要么是那种一心革命的小将,成日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要跟他切磋武功;要么就是新时代女性,留着短发,读书识字,精明干练,他不喜欢。
我知道,他骨子里还是喜欢那种传统的女人,柔情似水,温婉贤惠。可是都这个时代了,已经不好找了。他也便不想找了。
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很高兴,要家里老妈子整顿满满一桌好吃的,走时候还总塞我些银元零花。我知道,他是把我当儿子看了,我心中又何尝不是把他视作父亲呢?但是嘴上从来不说罢了。
知道他被红卫兵抓走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
社会已经被批斗得乱了,这我是知道的,每次回家,我也总是告诫父亲,不要惹事,在家里安心待着,莫要让人抓住把柄。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首先被抓起来的,居然是二爷。
“他是当过兵的!”我托了好多关系,找到了那个团体的头头,跟他分辨道,“解放南京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在前头,后来抗美援朝,他的命都险些都丢在了鸭绿江畔的土地上!你们凭什么抓他?”
那个跟我同龄的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我见惯了的狂热光芒:“他成分不好,是土匪,是地主,是资产阶级!我知道他的事情,他是反革命的!”说着,他手一挥,身旁的小将抬出了一杆枪。我认得这杆枪,白蜡杆子,点钢枪头,还有一撮飘舞着的红绒,这杆枪陪我度过了大半的童年,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除了二爷。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他指着枪尾处。我心里咯噔一声,暗骂自己怎么忘了这一茬,这把枪原本乃是清朝一位贝勒爷的宝物,因为武功显赫,御赐了三把枪,分别是混铁枪,白蜡点钢枪,盘丝枪。后来这把白蜡枪落在了张家的手里,别的倒也没什么,唯独要命的是,枪尾处阴镂刻着“御敕”二字。
“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与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张老二居然私藏封建残余,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他趾高气昂地说道,狠狠地一把把枪扔在了地上,唾了口唾沫在上面,又踩了两脚。
我感觉到自己的眼角跳了一跳,胸口的怒气逐渐溢满。
“不过……”他话锋一转,“你可以去劝劝他。只要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地主老财,是土匪山贼,当众悔过,接受批斗,他也还是可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的嘛。”
于是,我被带到了关押二爷的地方。
那是一个土塘子,时已入深秋,冷风逼人。塘子里的水漫到了膝盖的地方,二爷半身浸在水里,浑身都是被皮带抽打过的伤痕,脖子上挂着木牌,铁丝深深陷进了肉里,双手被拷住了。他闭着双眼,面色如常,只是嘴角紧紧抿着,带着几丝苦纹。
“二爷?”我忍住眼角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小声唤道。
他慢慢睁开眼,看到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来……你来干什么?快走,快走!”他已经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嘴唇发白,声音中透着一股虚弱。
我看着他的眼睛,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一下落了下来。
“你怎么不打啊,你打啊!他们哪打得过你?你怎么就这么被关在了这里?”我紧紧咬着牙关,泣不成声。
“傻孩子……”他竟然还笑了笑,“我如果打了,就真成了反革命了。我是当过兵的,为新中国流过血,卖过命。他们能诬陷我一时,还能诬陷我一世不成。我就等着看这些跳梁小丑,到底能欢腾到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在土塘里的二爷,那些劝说的话竟然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我看着他单薄的身子,竟像极了一杆宁折不屈的钢枪。
没想到的是,这次一别,整整三十年,我都没有再见过二爷。
那时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即使是我以大学生的身份,所做的也及其有限。后来我试了几次,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二爷,听说他死活不肯招认,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张二?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他啊。那次批斗的时候,我拿着铁棍,问他招不招,他不招,我二话不说,当头给了他一记狠的,嘿,你说这丫的也真是硬挺,鲜血顺着脸流了满身都是,他硬是没吭一声,嘴里还哼着曲儿。”
邻家的三胖儿在我跟他打听二爷的时候,一边喝着酒,翘着二郎腿,一边这么若无其事地说道。我眯了眯眼,当时没说话,三天之后,三胖儿被人发现扔进了粪坑里,打断了一条腿,他发疯了似得寻找凶手,可是得罪的人太多,始终没能查出到底是谁干的。
后来我随着父亲离家避难,去了邻省的一个大城市投奔伯父。没过几年,拨乱反正正式开始,父亲也恢复了教授的身份,我则选择了从事新闻行业,那时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在伯父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相恋半年之后,便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结婚的时候,我惦记着二爷,托人回老家打听了一下,没有人知道二爷的消息,仿佛这个人便从人间蒸发了似得。
后来生活渐渐步入了正规,儿子呱呱落地,父母相继辞世,我陆续托人回去问过几次,始终没有二爷的信儿出来,我的心也便渐渐淡了。
那把枪倒是被我找了回来,放在家里的储藏室里。儿子小的时候顽皮,不知道怎么给从角落里翻了出来,嚷嚷着非要我舞给他看。我心中一动,找了个晴朗的天气,把枪给仔仔细细擦了一遍,带着儿子就到了公园去。
进身,退步,抽,打,戳,扫,青龙出水,震脚……一招一式,从我的手中施展开来。初时尚且生疏,到了后来,往事历历在目,在眼前走马灯似得浮现出来。二爷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在耳边响起,从来不曾这么清晰过。手中的枪招越使越顺,我蓦地大喝一声,抽枪反身,一下刺进了身后草坪里,枪尖深深没入土里,只露出了一截红缨。
“好功夫!”我正喘息着,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喝彩的声音。我回头看去,一个灰褂老者背着手,须发皆白,正含笑看我。我摇了摇手,谦道:“小时候胡乱练过几招,多少年没碰了,手生,老爷子见笑了。”
“这可不是胡乱练的。这么正宗的五虎断门枪法,我有好几十年没见到过了,手生看得出来,底子扎实也看得出来,教你这路枪法的,可是个高人啊。”他抚须呵呵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二爷这路枪法的名字,不由问道:“老爷子,这五虎断门枪,有什么讲究吗?”
“这枪法据说是杨家将里的六郎所创,现在武术界流传的,大多是少林寺的传授,共四十六路,又叫少林五虎枪。你这套却不一样,是杨家的原版,只有二十七路,但是更加狠辣,我这么多年来,也只在年轻时候远远见过一次,从你手里使出来,算是我第二次见了。”
我心中一跳:“不知道您上次见到,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呵呵,你们年轻人恐怕想不到,那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老爷子摆摆手,转身走了。我愣在了当场,只觉口干舌燥,想要喊住老人,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口。
转眼又过了十年。
我临危受命,被报社老总派下任务,去采访完成一篇关于城市钉子户的深度报道。接到任务之后,我马不停蹄地奔波了起来,花了大半个月时间,采访逐渐进入尾声,最后一户人家,是邻省某市的一个新开发区,恰好离我老家不远。我选了这个地方作为最后一站,也是存了采访完后顺便回去看看的心思。
在资料上,钉子户姓常,是个孤寡老人,已经七十岁高龄了。我担心老人家脾气古怪,不好打交道,于是一大早,提了些新鲜水果礼盒,先准备去他家里碰碰运气。
一进门,左侧的土墙上挂着一个褪色的鸟笼,我心中忽然一动,好像在哪儿曾经看过似得,一股莫名熟悉的亲切感觉涌上心头。房屋不大,两进的老户型,中间是个小小院子,还种着一棵歪脖子枣树。常老正在树下洗漱,背对着我,穿着白色的汗衫,身形瘦削,微微佝偻,满头银发。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这个背影我却仍然能够一眼认出来。
“二爷?”我不敢置信地喊道,手中的水果掉在了地上,我瞪大双眼,以为自己活在梦里。
他身子一震,缓缓回头,那张饱经沧桑的老脸上皱纹纵横,依稀可以看见年轻时的英挺模样。他看到我,皱紧了眉头,似乎认不出来,半晌才露出惊喜神色,哑着嗓子问道:“小方儿?”
我哈哈大笑,兴奋地一把把他抱了起来,大声喊道:“二爷,二爷!我找了你整整三十年了!”说着说着,我鼻子一酸,竟险些落下泪来。再看二爷的时候,他也是激动异常,紧紧抓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
我打电话叫了隔壁小饭店送了桌酒菜来,二爷拿出两个小木凳,我们爷儿俩就坐在了歪脖子枣树地下,举杯对饮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二爷已经落下了浑身的病根,他回家之后,发现屋里家徒四壁,除了一个鸟笼之外,几乎都被人摸了个干净,什么都不剩下了。他拖着重伤疲惫的身躯,一合计,觉得不能再在本地待着了,干脆把宅子贱卖了,收拾行李,搬到了隔壁市的远郊来。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我问二爷靠什么过活,他说当年学着他老爷子,早在遇难之前就在家里地砖地下埋了几根金条,几件珠宝,取出来慢慢变卖了之后,倒也凑合着过了下来。后来国家统计退伍老兵,他也递交了申请,现在每年能拿到500块左右的补助。
我不由大怒:“500块?哪能够干什么的!二爷你别怕,我去帮你向上反映,你是立过功的,国家不能这么亏待你!”
二爷却摆了摆手:“什么立过功?都是上辈子的陈年旧事了。日本鬼子没弄死我,旧社会的内战没弄死我,平壤的美国枪炮没弄死我,十年动乱也没弄死我,过去的老伙计们还有几个活着的?我已经知足了。现在能安安分分有个家,过个小日子,还图什么呢?以前惦记着放不下一个你,老天可怜见,还是让咱们重逢了,现在就是下一秒进棺材,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仔细问了二爷关于钉子户的事情,他狠狠啐了一口,骂道:“这狗日的黑心肠,我大半辈子熬过来了,就剩这么一个窝,他们还得给拆了。要是拆了给个安置的倒也算了,他们想欺负我年纪大了,随便给两个钱糊弄一下,把我送到敬老院去。我还就是把话放在这儿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别想给我把房子给拆咯!”
我心里“咯噔”一声。这个建筑商的背后老板在我们传媒界是素有耳闻的,据说黑白两道通吃,拆迁安置的时候,一般都是双管齐下,软的不行来硬的,之前有过不少钉子户被黑社会威胁,甚至拿刀架了出去,一回头,发现房子已经被扒成了废墟。如今二爷跟他对着干,岂不是危险的很?
我连忙问道:“二爷,那你不搬,有没有人来找过你的麻烦?”
“嘿,倒是有几个小年轻来找过。谈不拢就想动刀子,二爷我是什么人,美国大兵都没能拿我怎么样,几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咳咳,喝酒,喝酒……”
那天晚上,我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依稀记得是二爷把我扛回了房间的床上,迷迷糊糊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次晚上玩累了,趴在院子桌上睡着,二爷就这么把我一扛,扔进屋里床上睡去。
“二爷……”我半醉半醒之间,低声喊着,“你再教我几招枪法呗……”
耳畔依稀传来苍老声音:“枪法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什么好教的了……剩下的就是练气了,你身上得藏着一股气,这世道多苦啊,人想要活着啊,就得靠这么一股气的劲儿……”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二爷躺在藤椅上,已经走了。面容安详,带着笑意,右手五指虚握,仿佛还抓着一杆白蜡长枪。
死因是寿终正寝,但我给二爷换寿服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肚子上有一道新添的刀伤。我心中一沉,登时红了眼睛,托尽了关系,才找到了当地的公安局长。
他听我说起二爷死因,半晌没答话。
我说局长我没别的意思,二爷从小待我,跟亲儿子没什么区别,现在我这是死了爹了。如果连他是怎么死的我都弄不清楚,我这当儿子的,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
他叹了口气,说好吧,我给你看个视频。
视频很模糊,似乎是街边摄像头拍到的。正好对着二爷家的门口,时间是五天前的凌晨一点。几个黑衣服,金链子,混混模样的年轻人堵在了二爷的家门口,视频里没有声音,但看他们的神情举止,不难猜出他们在威胁些什么。
二爷穿着白日里的那件大汗衫,身子微微佝偻,手里拿着一根晾衣杆,似乎在给自己壮胆。那几个年轻人嬉笑不绝,似乎觉得这么个老头子还拿着棍子,有些好笑吧。
忽然,为首一个年轻人走上前去,抽出刀,想用刀面去拍拍二爷的脸,这似乎是他们一贯的威胁手段。就在这时候,视频一个模糊,二爷似乎动都没动,那年轻人已经捂着手倒在了地上,刀也不见了踪影。
我觉得自己的呼吸停了一停。
耳畔似乎传来了很多很多年前,二爷的声音:
“……跟一头熊似得,大吼一声,就冲我扑了上来,我抽身错步,枪尖那么一点,嘿,他那匕首就飞了出去……”
“……要知道我们习武之人,练到后来,就是追求的一个‘惊’字,所谓惊弓之鸟,就是你刚拿弓箭对着我,我就能感受得到,下意识地做出反应。听起来玄乎,但就是这么个道理……”
“……身后还有一个美国佬,拿着军刺就扑了过来,我比他更快,猛地向前一突,他还没刺上我,眼珠子就瞪了出来,被我一棍戳中了肚子,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视频的像素太低,就像是最拙劣的影视制作一样,看不清楚二爷究竟干了什么,只一瞬间,所有年轻人都倒在了地上。二爷慢慢走过去,蹲下来,好像想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候,为首那个年轻人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狠狠划了过去,二爷想退,却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几个年轻人趁机爬起身,转身就跑。二爷倒在地上,右手捂着伤口,慢慢地,慢慢地,挪到了墙角,靠着喘息了一会,然后脱下汗衫,给自己简单包扎了一下,才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走进了屋子里。
整个过程中,二爷的右手,都没有松开过那根晾衣杆,好像那已经长在了他的手心里一样。
我闭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局长,那个凶手能抓到吗?”
“你放心,我们已经拍了专门的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情,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满意……吗?
我无声地笑笑,微微欠身:“那谢谢局长了。”
我把二爷的骨灰带回了家里。
在市内最顶尖的公墓陵园里,我给二爷定了一个位置,把它的骨灰连着白蜡点钢枪一起埋了进去。
儿子在一旁静静看着,忽然问我:“老爸,这就是教你枪法的老爷爷吗?”
枪法?
不。
我摇摇头。
“他教我的,不是枪法,而是气。练枪就是练气,只有把气练好了,人这一辈子,才能活出个模样来。”
1/7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