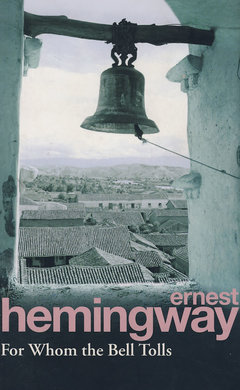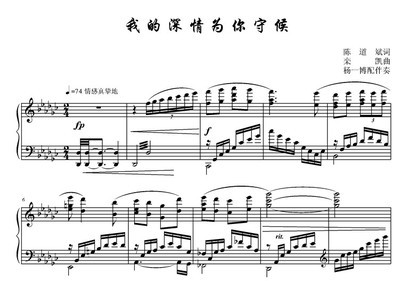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又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无我之境_无我之境 -概念解释
“无我之境”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
无我之境_无我之境 -出处及分析
王文生先生说:“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心物交融的结果。说‘有我之境’,是文学的基本现象;说‘无我之境’,则是文学中从未存在的境。……以‘我’之有无作为境界的划分显然是行不通的。”(P32)
“诗中无我,诗无面目”,诗中有“我”的确是“文学的基本现象”,遗憾的是王先生对“无我之境”作了误读,发生了误解,以为“无我”即“没有我”。
王国维“无我”的本义是“无欲之我”,源自他所作《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其云:
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夫空间时间,既为吾人直观之形式;物之现于空间皆并立,现于时间者皆相续,故现于空间时间者,皆特别之物也。既视为特别之物矣,则此物与我利害之关系,欲其不生于心,不可得也。若不视此物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观其物,则此物已非特别之物,而代表其物之全种;叔氏谓之曰“实念”也。
原来他将“吾人”所观之物分为两种:“特别之物”和“非特别之物”,前者是容易引起观者发生利害关系的思考,后者则使人可超脱利害关系,但观其美“之种类之形式”。将“观”也分为两种:“特别之我”与“非特别之我”,前者是有“生活之欲”的“我”,后者则是“纯粹无欲之我”,对所观对象没有特别要求的“我”(不要求“物皆着我之色彩”)。后来,他作《人间词话》时,将有“生活之欲”的我简化“有我”,将“纯粹无欲之我”简化为“无我”。这一简化,尤其是“无我”的简化,百年来使不少学者和读者产生疑惑和误解。(注:季羡林先生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先生把它列入无我之境。我认为,实际上是有我的。汉文可以不用主语,如译为英、德、法等文,主语必赫然有一个‘我’(l,ich,je)在。既然有个‘我’字在怎么能说是‘无我’呢?我觉得,在这里不是‘无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观物’,而仍然是‘以我观物’,不过在一瞬间忘记了‘我’而已。”《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其实,“有我”与“无我”,关键在于观者的心态与情态。“有欲”而观,观之对象就成了“特别之物”;“无欲”而观,同一对象也会成为“非特别之物”。有“生活之欲”的耸动是“动观”,无“生活之欲”干扰而沉着镇静是“静观”;“有我”是特定主体之我而观而言情,所以会是“物的人化”;“无我”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会是“人的物化”或“情的物化”。“有我”与“无我”,皆有“我”有“情”,不过因“我”之立场地位不同与情感方式不同而如此区分罢了。
无我之境_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钱钟书先生有更精细的论述,他在《谈艺录》的“附说九”(注:《谈艺录》53-56页,中华书局1984。)中,从李贺诗“好用‘啼’、‘泣’等字”,推而论山水诗。他说,有不少诗人的山水诗“虽情景兼到”,但“我”与山水“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所指的是诗人移情于山水,这类诗“皆不过设身处地,悬拟之词”。有的山水诗则“境界迥异”:“要须留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前一类,明显是“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后一类,属于庄子“万物与我同一”,但还只是“情已契”,是否属“无我之境”呢?且看他又从郭熙论画山水道来:郭之“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云云,即是“瑞士哲人亚弥爱儿(Amiel)雨后玩秋园风物而悟‘风景即心境’。”将客观风景就看作我的心境,这个我,“乃喜怒哀东未发之我虽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乃无容心而即物生情,非挟成见而执情强物。”这无异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丧的“执情强物”之我,更是王国维所说不计“一己之利害”的“非特别之我”。钱先生举了比王国维更完整的实例,一是李白《赠横山周处士》:“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二是苏轼《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注:这样的实例,还可举李白之《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词前小序云:“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苏轼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中化蝴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此之谓物化”,实已道着“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人的物化”或“情的物化”,亦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最道出有我有物、非我非物的境界”。此境界即是地道的“无我之境”。
王先生欲以“移情之境”、“融情之境”来取代“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说“二者都是有我之境”,但观其所举“融情之境”的典范作品,如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姜夔词《点绛唇》“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陆游《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及其理论表述:“似无意写情,而情意绵绵;不刻意写物,而极尽物态。情物融浃,妙然无迹。可达到了‘无迹之迹诗始神’的高格。”(P186)窃以为所举诗词的确达到了情景高度交融的境界,但是,此情之主体显然不是“纯粹无欲之我”,其情非“自然之情”,“泪始干”、“清苦”、“愁”是“特别之我”的特别之情,属“有我之境”无疑,与“有我有物、非我非物”之境迥异。因此,“无我之境”实不能取消。
弄清了“有我”、“无我”,再回头看“写实”与“理想”是否同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写实”固可与“有我”的现实主义相通,而“浪漫主义”有强烈个性的“我”在,从叔本华到王国维的“理想”只是“合乎自然”,应归属于“无我之境”,与“浪漫主义”无缘。这就不证自明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