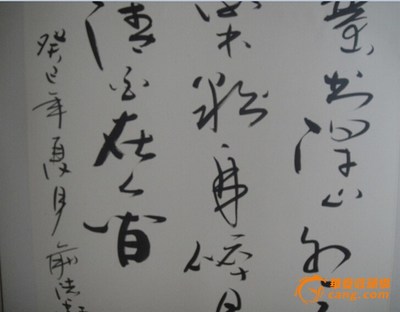傅惟慈,满族。文学翻译家。曾用名傅韦。北京人。1923年生于哈尔滨。傅惟慈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但当年他选择翻译却是为了忘记残酷的现实。1978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把《问题的核心》基本译完了,有几个公司名称的缩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翻译的时候最怕碰到一个国家有特色的东西,就向国外的朋友写信请教,这个朋友替我给格林写了封信,不久,他就回信了。
傅惟慈_傅惟慈 -简介
50年代从俄语及德语译介了匈牙利、波兰等国当代文学作品,从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任理事。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德〕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傅惟慈译作
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着,曾两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此外,他编选的《冯尼格黑色幽默作品选》、《一支出卖的枪》等文集同样影响巨大。
傅惟慈_傅惟慈 -诗人
傅惟慈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但当年他选择翻译却是为了忘记残酷的现实。其实很多文学家都有
这样的经历,比如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不能发表作品时只有靠翻译为生。或许历史是一个玩笑,不过许多伟大的翻译家正是出自这种残酷的现实。
年轻时候,我对文学有梦想。做翻译是为了忘记当时残酷的现实,也不排除是为了想表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可是在“文革”中,我差点儿戴上了一顶诗人的桂冠。
“文革”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比较受宠,因为我善于“钻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德语文学名着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着”,共100多本,其中我挑选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来翻译,从此开始有些名气。因为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文革”前两年,我突然被安排到资料室去打杂,没有了登讲台的资格。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些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我想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最大的罪名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吧?
有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看大字报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里翻资料。一个年轻的法语老师突然走进来,对我说:“没想到你还写诗。”我说:“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他告诉我说学校有张大字报说我写反动诗。几天之后,看到他给我送来的一张纸条,我才恍然大悟。纸条上面写的是:“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在那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我帮他们翻译一些德文诗,都是指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内容。我常常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第二天偶然想到该怎么翻译就随手记在本子上。后来这个本子不知怎么回事丢了,过了几天才从系里的秘书那儿领了回来,没想到就在这几天里他们把我的笔记本当中的几页拍了照片存到档案中。
假如没有那个年轻老师的通风报信,我还不知道我“反动诗人”的黑锅还要背多久。幸亏我还保留有出版社的约稿信。我提交了申诉后很久,系里的领导小组找我去谈话,说我写反动诗的事情已经解决,但还是要继续劳动,其中一个人说:“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
傅惟慈_傅惟慈 -不喜悲剧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和格林连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今年是格林诞辰100周年,但十多年来格林的宗教小说和惊险小说对中文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没有傅惟慈,我们就不会这么深入格林的世界。
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我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面,整理资料、分发报纸,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幸好,这个时候学校从英国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外教,他带来了上百本的英文书,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了供老师借阅,当然我还要负责看看书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内容。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听说过或者连名字都没听过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包括《问题的核心》和《一支出卖的枪》。格林的书很多都是以悲剧结尾,其实我不喜欢看悲剧,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鸵鸟一样,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但人生路上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还是有走到绝路的时候。
《问题的核心》讲的是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我自己当时在资料室里工作,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内心很苦涩、很灰暗,读到这本书当然感触很深。
虽然说我写反动诗的罪名澄清了,革命领导不能把我打成反革命,但又不愿意让我回到人民队伍中去。1968年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那些木工们干完活就钓鱼、打扑克牌,没人管我。跟我住一间屋子的木工每天都回到几里以外的家里去住,所以对我来说这儿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
就是在木工班的宿舍里面,我又把《问题的核心》专心读了很多遍。1979年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除了是对我自己的纪念之外,我还抱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了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折磨的人不止他一个。
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书里面,邪恶的势力总是战胜美好的事物。有时我想,格林看到的社会阴暗面是不是太多了?也许是吧,但是我们社会里面的危机还少吗?
傅惟慈_傅惟慈 -谈格林
就翻译来说,译者和作者的交流永远是重要的,这种交流有可能带来原着的真正精神。
从这个意义出发,傅惟慈和格林的交往绝对不是一次会面那么简单,其实更多的是两人之间的精神契合。只是不知道,《格林文集》何时能够面世。
格林本人不像他的作品那样低沉,他看起来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我同格林通信是在1979年的春天。1978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把《问题的核心》基本译完了,有几个公司名称的缩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翻译的时候最怕碰到一个国家有特色的东西,就向国外的朋友写信请教,这个朋友替我给格林写了封信,不久,他就回信了。1980年这本书出版后,我给格林寄去了一本。
1981年年初我到德国,又跟格林通了信,他表示他愿意跟我在欧洲某个地方相会。
当年的9月左右,我有1个月的假期去英国。格林的家在地中海的某个避暑胜地,不过一年有两三个星期会回到英国处理一些出版的事情。
恰好当时我们都在伦敦,他就约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了一面。那一年我55岁,他78岁。他精神状态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而且很热情、爱开玩笑。
他喝威士忌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我还在喝第二杯橘子水,他说:“你只喝一些软饮料吗?中国的茅台可是世界驰名的。”和他在一起,你一点都不会感到拘束,他很健谈,但是绝对不会把话题全部垄断。
他问我中国人对他的作品了不了解,可惜我回答不出来。我只能告诉他,《一个沉静的美国人》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但是这以后20年,只有一个短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直到80年代,中国的读者才逐渐知道英国有个格林。
当时格林还对我说,他并不太喜欢《问题的核心》,虽然这本书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据我猜测,他可能是觉得这本书不够深刻,小说里的悲剧感很能打动一般人,但是对人性的挖掘不够。他说他更喜欢《荣誉领事》(《权利与荣耀》)和《随姨母旅行》。
到1987年的时候,我又见过格林两面,谈我想在国内出一部20卷的《格林文集》,他很高兴,答应给它写序,还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为止我没有实现对格林的承诺。
傅惟慈_傅惟慈 -翻译之旅
翻译家选择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比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或者傅雷的巴尔扎克,傅惟慈最心仪的作者无疑是格林和毛姆二人。对这位热衷旅行和钱币、足迹遍布全球的翻译家来说,翻译恐怕是另一种旅行方式。
1990年的时候,我在四川碰到一个小青年,他背个大包,带着300来元钱就想一个人去西藏,说是受了艾芜的《南行记》的影响。我对他说:“你不现实!”但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是个生性喜欢东奔西跑的人,小时候读到艾芜的《南行记》和高尔基的《俄罗斯漫行记》,让我特别向往。
我20岁的时候也一个人离开了家,说是想到前线去抗日,实际上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我喜欢那种离开现在的感觉。可惜我生不逢时,一辈子有太多时间被耽搁在政治运动中。
1987年4月,我在从希腊的萨洛尼卡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奥地利朋友,我们谈到中国、奥地利,也谈到文学。他是一个写作迷,我说一个人对演奏或者写作着迷,可能是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他说他从没想过要表现自己,开始是怕忘记一些事情,后来写作就成了癖好,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写了。
他让我想起我翻译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小说里面的“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怪行后问自己:“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写下去。”我的奥地利朋友就是一辈子一本书都没出过,还是坚持写作。我想,如果我翻译了一本书,但是知道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出版的话,我不会做这个工作,因为如果单纯为了自娱,我不会去做翻译,我会去玩、去旅游和收集钱币。
傅惟慈_傅惟慈 -记者手记
傅惟慈
先生的家在西直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独门独户的小院,院里栽种着些植物。家里是不通暖气的,要取暖全靠空调。这是先生家祖传的院子,他从1951年住到现在有53年了,免不了担忧可能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命令,这是他最感愤恨的。
先生起先不苟言笑,谈到他搜集的钱币的时候才面色柔和,把收藏钱币的册子一本本拿出来给我看,说常常有同好者来欣赏,还有商家想要收购他的一些钱币,而他是断然不会出售的。
即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突然说你等等,你来看看我的这间屋子。
他带我去看的是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着的照片,都是他在国外旅游时候拍下来的,放大了镶在镜框里。说起在外游玩的经历,他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来。
格林的书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原因之一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黑非洲,他说他从童年开始就喜欢神秘的蛮荒之地,喜欢探险,喜欢惊险小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