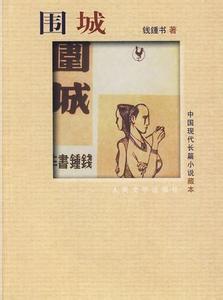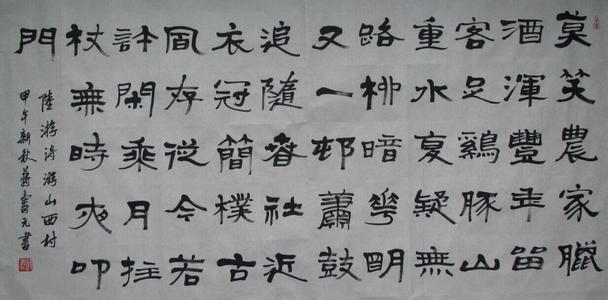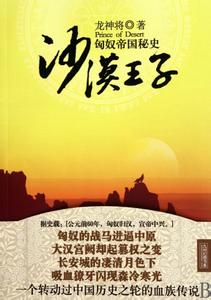《纽约琐记》是陈丹青90年代后期出的第一本散文集,是陈丹青纽约生涯的结账,初事写作的开端。
纽约琐记_《纽约琐记》 -概述
作 者: 陈丹青
《纽约琐记》出 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几位相熟的读者批评说,近年我所出的三五本“书”,还算《纽约琐记》尚可读。这本书是我纽约生涯的结账,初事写作的开端……我的生活因这本书从此转向,出现新地带。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在博物馆凑近名画合影留念的青年,回国数年,也和那位《纽约琐记》的作者日渐疏远: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
纽约琐记_《纽约琐记》 -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
纽约琐记_《纽约琐记》 -内容欣赏
第一部分
《纽约琐记》
《纽约琐记》
1992年夏末,我同定居西岸的几位中国画家在“加州艺术学院”办展览。据说在西岸所有大学中,这是唯一允许在校内游泳池裸体游泳的学院。由于我来自东岸,校方安排我住在学院客寓。一位职员引我入住时,特意介绍这里曾经招待过哪些学者名流,我没心思听:大约二三十米外,就给我一眼瞥见那座池水碧绿的游泳池。
第1节:艺术教育(1)
艺术教育
1992年夏末,我同定居西岸的几位中国画家在“加州艺术学院”办展览。据说在西岸所有大学中,这是唯一允许在校内游泳池裸体游泳的学院。
由于我来自东岸,校方安排我住在学院客寓。一位职员引我入住时,特意介绍这里曾经招待过哪些学者名流,我没心思听:大约二三十米外,就给我一眼瞥见那座池水碧绿的游泳池。
职员走了,我赶紧朝池子方向仔细张望:果然,女同学、男同学,不着寸缕、赤诚相见。
但引这两句中国成语,并不贴切。前一句从言情小说里读来,字面即淫,此刻我看见的只是“身体”,非常简单,就好像不带形容词的主语、单词;后一句并不指身体,是当年我们这伙男知青在农村河沟赤条条洗澡时,用来彼此调笑的成语,算是形容“光着身子见面”。但那群裸体的美国男女“知青”并没在互相看,各人只顾自己专心地划水、晒太阳、斜在池畔看书。
是我在偷窥――这个词也不贴切。游泳池设在教学大楼和我客寓之间一片露天空场当中,周围是草地、棕榈树和甬道,走过池边的师生个个若无其事,还有人被池中同学大声叫住,停下来聊天。
“裸体”(nude)、“袒露”(naked)这两个英文词都不涉“性感”,论性感,那是鲁迅关于“从白胳膊到全裸体”的中国人的“想象力”。此刻我瞧着这些“全裸体”,想象力全部停息,只顾眼巴巴地看:在水

《纽约琐记》中,池畔,年轻人的身体真好看!
三十多年前,我有幸被上海游泳队区儿童班培训四年。将要升入市少年班时,我被除名了。事后教练偷偷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将来出国比赛,外面有人,也就有可能叛逃的。
加州的阳光。阳光也“裸体”。可我实在不好意思脱掉裤衩。赶紧下水埋头游泳,游完,赶紧湿淋淋回客房。看来给亚当胯下画片叶子是对的,去掉叶子,他就不害臊了。
“加州艺术学院”的名声,不是裸泳,是只教“理念”,不教画画(80年代大红大紫的后现代画家萨利、费希尔却在这儿毕业)。自然,学院展览馆也展画,校方照例派两位同学帮我们将画上墙。男的是白人,女的是华侨子弟,晒得黝黑,活像我插队时的知青女标兵。“学校教些什么?”我问,指望能听到一番高明的说法。不料她一句话就打发了:
第2节:艺术教育(2)
“就教我们怎样思想!”
隔天我在游泳池遇到那位男同学:他先叫我名字,我才认出来,因为他裸体。罗丹的那位“思想者”倒也一丝不挂。
在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有一所老牌名校叫做“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美国现代艺术的祖母级人物乔治娅・奥基弗曾在此毕业,日后成了美国女画家的偶像。闻一多先生早年也在“联盟”留过学,闻先生的二公子,我的老师闻立鹏先生曾嘱我在校内外拍些照片作纪念,我就拍了,寄去北京。
“联盟”自50年代后渐渐没落。她成了一所向各种年龄、身份艺术爱好者开放,但不颁学位的古董型美术学院。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旧白楼和至今地处五十七街昂贵地段,可以证明她往昔的光荣。
校内挤满艺术学生和业余爱好者。80年代,中国人来了,仅仅为了学生签证而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先是心不在焉混在各国学生中画人体素描。一边画,一边为下个月的房租犯愁。模特儿却是个个认真敬业,不必老师摆弄,自己做各种姿势。但我以为不好看,不入画:健美把式?体操动作?还是舞蹈造型?看来希腊传统远在地中海,美国还是美国。一位肤色雪白的健硕男模特还有绝活:他一弓身倒立起来,面红耳赤,神情坚毅,维持将近一分钟。
他的女友在别的班当模特儿。有一天他抱着新生婴儿来到教室,全班鼓掌欢迎。
我是个坏学生。进了教室我就沮丧、瞌睡。后来索性每天到门口签个到,就溜上三楼咖啡座抽烟。
在咖啡座,天天可以看见一位满头金发、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她的样子仿佛尚未卸装的百老汇歌舞演员,过时太久的时装模特,或被遗弃而曾经有身份的女子:旧式女帽斜插着一支紫色羽毛,衬领敞开,露出垂老的乳沟。超短裙碧绿,更其碧绿的连腰网眼长丝袜,当然,还有颤巍巍的,但完全不适合她的年龄的高跟鞋。如同许多上东城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她的神色,以至整个身姿流露出经年累月的凄凉和高傲。她从不看人,也不同人
《纽约琐记》说话,永远孤零零地占据着门边一张椅子,威严而茫然,凝视着桌面上的咖啡杯,或者弯下身照料脚边的几只塑料袋。
第3节:艺术教育(3)
她不像是做过母亲或妻子的妇女。这在纽约并不稀奇。显然她也不是这儿的学生,咖啡座侍者说,上几代的雇员和学生就看见她天天出现。不消说,她是疯子。此地的人从不打搅疯子,学校也任由她进出流连。可纽约有得是乞丐或半疯的人――学校对过就有一位既疯且醉的壮汉,每天高声歌唱普契尼咏叹调,手里举着讨钱币的铁罐――这位老太太何以偏要到“艺术学生联盟”来?
但愿后来我听到的故事是真的:终于有人告诉我,马蒂斯50年代造访纽约(这事是真的),据传曾选中这位女士当模特儿,也就是说,大师本人画过她。
难怪她骄傲。难怪她喜欢紫色和生葱般的绿色。在毕加索第五位未婚情人吉洛的书中,我才知道(而不是从画中注意到)马蒂斯最钟情的组合就是这两种颜色。原来她是忠贞不渝的艺术烈女,这位紫绿色的缪斯!
常在美术馆遇到各色肤发的儿童,席地坐开,好像一群拦路小狗,你得绕开。老师正在讲解。美国儿童喜欢争先恐后举手发言:“彼得、安琪拉、罗森奎尔!”所有孩子对老师直呼其名。
母亲推着童车逛美术馆。如果是双胞胎,就有双座童车,并排坐好,一人含着一个塑料奶嘴。有部好莱坞片子给香港翻译成《窈窕奶爸》,真的,我好几次看到青年男子袋鼠似的当胸用布袋兜着个熟睡的小毛头,面对名画,做沉思状。
“艺术胎教”?暗幽幽的美术馆于是好像巨大的子宫。
纽约有两所艺术高中。一所是“拉瓜第亚艺术高中”,设表演、美术、音乐、工艺各专业,地点在上西城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左侧。一进大门,前厅半壁好莱坞明星照片。凑近细看,原来注明是该校历届毕业生。仅举一例:艾尔・帕契诺,电影《教父》中饰演老三,在上集片尾当上教父的那位相貌冷酷、目光如炬的大演员。帕契诺如今五十多岁了,不知在这里念高中时,脸上是不是那股狠劲儿。
另一所是“艺术与设计高中”,在上东城二大道。我的女儿就读这所高中,入学第二年就开电影课。她回家问:“看过俄国片《战舰波将金号》吗?那是蒙太奇的经典。”我说:“没有,不过你可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她说,没有。
昨天她在饭桌上宣布:老师告诉他们,萨尔瓦多・达利,70年代曾到这所高中讲演,地点就在上
《纽约琐记》个礼拜我去看孩子97年度时装表演的大礼堂。
一所高中能请到达利。达利也愿意去一所高中。那时老先生快八十岁了吧,老师说,达利走进礼堂时,手里牵着一头活的金钱豹。
1997年6月
第4节:绘画的观众(1)
绘画的观众
1996年5月,塞尚大展在费城美术馆开幕。
去费城方便,订票麻烦。除了预订日期,还得听从馆方安排进场钟点,观众不能太挤,而外地的观众则要算计来回时间。
占线。老是占线。费城美术馆这样的大户,居然只有一条订票专线。纽约的大馆每有专展,至少两条以上,雇员也多。都是经费问题。难怪美国人说费城没落了。可是要看塞尚精品,全美就数费城最集中,尤其是城郊的邦尼收藏馆,连欧洲人也得专程来拜,譬如这回大展,年初在巴黎开办后,径来费城,倒好像费城是塞尚的娘家。
6月底,还是占线。7月初全家回中国,机票早订妥的。在纽约,光是华人经营的旅行社就有上百家――旅游生意到底比文化生意做得好,也好做呀。
回到中国,我就忘了塞尚,忘了美国。晒在京沪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感觉是根本没有离开过。
8月下旬。回纽约翌日,刘索拉来电话。他们夫妇俩隔天要去费城看塞尚展,邀我同行,行程安排是下午先往普林斯顿大学斯丹利先生家做客(票就是他弄的),傍晚同车去费城――票子规定六点进场。
得来全不费工夫。第二天我们上了去普林斯顿的火车。
索拉的丈夫阿巴斯任教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常来纽约,同研究卡夫卡的斯丹利是老朋友。一小时车程,我们小半在谈这位教授的婚姻。下午将见到的第五位太太是德国人,据说斯丹利相中她是为一房19世纪古董家具的陪嫁,她呢,大概就为夫家的这份教职吧。事成,斯丹利给阿巴斯去电话:“家具快运到啦,可是老天,人也一起跟来!”
第5节:绘画的观众(2)
两点。斯丹利到站迎接。他五十开外,长得活像指挥家伯恩斯坦。他开口就是笑话和双关语,善戏谑的中国人自己并不笑的,斯丹利正相反,倒也照样逗笑:他先是一缩脖子,旋即就笑得没声音了,快要晕过去的样子。他也像伯恩斯坦喜欢大幅度耸肩,耸着,说完很长一段话,这才把肩膀放下来。
秋初天气,树叶还绿。他家在小树林子里,古董家具正隐在树荫投入室内的绿森森的幽暗中。家具也多绿色。欧洲人善用各种灰绿,同银色、暗红、乳白配在一起,显得饱和而克制。女主人意态娴静,面容像只鹦鹉,眸子灰绿色。她也是个笑话家,只在丈夫无声的噎住似的大笑之间插进几个单词(女中音,德国腔英语),就能引得轰桌大笑(索拉本来就爱放声大笑,高音),她自己则神色安然,隔着桌子问我画些什么,去过欧洲没有,说她也有个女儿,在维也纳上大学,她自己弄摄影,名字叫瑞吉娜。
四点钟我们移到后院坐。斯丹利指着林子另一端人家,长篇大论诉说同那家人的纠纷。中国此时是凌晨,“时差”开始发作。我于是请瑞吉娜给我看她的摄影作品。我不喜欢美国的树林,那只是植物,不是农村。塞尚在这儿会有画兴吗。不过他似乎不在乎景致,他画的景,别的画家未必肯坐下来画的。
《纽约琐记》
从普林斯顿去费城,一路夕阳。才不过几天前我还去了北京燕郊,大片玉米地,雨后牛蛙轰鸣。有人问塞尚最喜欢什么气味,他说,田野的气味。美国田野没有气味。在美东地区根本见不到真正的田野。
坐落在高坡上的费城美术馆岿然在望。塞尚从未来过美国。德加来过。在馆外有喷泉和纪念碑的广场上,特意为塞尚专展划出大片停车场。时差的倦意加剧,叫咖啡来不及了。六点进场,我强打精神。此地习惯,如果结伴逛美术馆,除非众人存心在进馆后继续痛聊,通常各人自便。斯丹利建议八点半在前厅右翼那尊罗丹《三男子》铜像下会合,然后一起晚饭。
第6节:绘画的观众(3)
好习惯。我喜欢独自看画。五分钟后,我们就在展厅人丛中分开,隐没了。
散在欧洲各国,包括从前苏联的塞尚藏品,差不多都借来了。见到殊少付印的作品(熟识的画家忽儿陌生了),见到名震画史的经典(总算验明正身),是看回顾展最快意的事情。观众拥挤,个个缓慢移步像在梦游。音乐会场的大静之中,难免有人咳嗽,重要的画展即便随时听得喃喃低语,却是一片寂静。在第七展室,塞尚五十岁前后那四幅苍老丰腴的静物分别悬挂在四面展墙上。人眼可以同时瞥见好几幅画,但脚步迟疑――先看哪幅?仿佛一场耳提面命的教训即将开始,又像是终于面晤单恋已久的人,这时,不是你在选择,而是它在夺取你的目光和神志。纽约有位抽象派老将回忆初次拜见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只看一眼,他就反身跑出展室,忐忑良久,这才回进去细读。
塞尚这几帧静物的尺幅不大(其实所有的画都是“静物”)。怎么办,时差逼得我头晕,不得不坐下来闭目休息片刻。《水浒》里写的迷魂药效,恐怕就是时差的感觉,脑筋混沌,双眼干涩,意识沉下去,沉下去。或许就是经典造成这轻微而明确的晕眩?再说展览限时入场,成百上千人远道而来,分批进场风雅两三个钟头,观看于是变为一项任务,一项过于郑重其事的仪式。萨特说,挤在音乐厅听音乐是荒谬的,音乐该独自倾听。绘画呢,同绘画的相处之道,最好是朝夕与共,经年累月,不必用心看,不必多看(经过,抬头,画在看你)。
今晚眼前的这些画曾天天同塞尚耽在一起。我看过在普罗旺斯老头子画室里拍摄的纪录片,只剩遗物了。“他每天工作,非常非常孤单。”解说员是好莱坞老牌明星道格拉斯。美国《室内陈设》杂志常刊印亿万富翁家藏名画的专辑。那才叫“金屋藏娇”,在客厅、书房和同样豪华的过道或浴室里,墙上挂着马蒂斯、毕加索,还有塞尚。不过对这类高尚其事的文化活动,我们理当心存感激。我们是公众(画布有知,终日面对公众,它可疲倦?),此刻趁着名典近在咫尺,好好看吧――“欣赏”是个什么也没说出的词。“解读”是个好词(好词立刻就被用滥)。“凝视”比较准确:静静地,狠狠地看,目不转睛。你在想吗(画只是“通过”眼睛)?其实是在发呆。看来大匠师的回顾展就是迷魂药。晕眩,是竭力试图清醒的意思。可是在伟大的艺术面前,清醒无济于事。
《纽约琐记》第7节:绘画的观众(4)
回顾展也有功德无量的一面。作者复生,真该自己来好好看看。他想必从未如此巡视自己一辈子的作品:他也会暗暗惊讶这么多作品全是他独个儿画出来的,好像有上百个塞尚,每幅画都有一个他在,一笔笔停着,凝视着我们这些陌生人。我们谁也不认得塞尚先生,就像他无缘见到他的观众。第八、第九馆的画就是他的晚境了。好几位大匠师的晚期作品看去像是疯了(当然也可以用“崇高”、“升华”这类字眼)。“疯”,是不是指出离常态?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据说是“炉火纯青”。阿多诺说:晚年的作品乃是一场灾难。
出馆。照例是专展礼品部,灯光大亮、人声嘈杂。除了他的画册(平装、精装),照例是将他的画面所制成的商品:大幅海报、中型画片、小画片、明信片;带镜框的、不带镜框的;幻灯片、录像带、拼贴玩具、魔方;画家故乡风景摄像集(重拍被画过的实景多扫兴,实景照片就像被画吐弃的渣)。当然,还有纪念章、领带、胸针、耳环、项链、首饰、丝巾、浴巾、瓷盘、陶器,等等等等,全印着他的画(面目全非,可不是他的画又会是谁),或他的签名手迹(字迹蜷曲着,伸缩在丝巾浴巾的皱隙之间)。
奇怪。时差的苦倦忽然消散。精神抖擞。
罗丹《三男子》足下空无一人。我不戴手表,想必早过了约定时间。警卫正在收拾入口处甬道两侧的丝绒粗绳。费城我熟悉。很快找到火车站,刚开走一班,下一趟将近零点。我走到站外抽烟。夜凉沁人心脾。要是在有蛙鸣有气味的田野该多好。
第二天打电话向索拉报告。她说,他们出馆后在一家土耳其馆子晚饭,说了好多笑话,并去斯丹利家过夜。在二楼书房,还为我安排了床铺。她问我画展观感如何。真的,除了时差的困倦,以及在那几幅静物画前努力睁开眼睛的记忆,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喂!塞尚,塞尚先生!你好吗。我来看过你了。我们诚心诚意来看过你了。
1997年6月
第二部分
《纽约琐记》
《纽约琐记》
带天窗的画室早已不时兴了,同架上绘画一样,成了古董。纽约艺术家的梦是租用老式工厂仓房整层打通的大画室(英文叫做“Loft”),面积两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转。如果在苏荷一带,月租三五千。再花个几万装修,隔成画室、书房、卧室,然后买来中东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欧洲的古玩――“Loft”其实不仅是画室,它代表后现代的生活方式,纽约上流文艺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叠高额账单。
第三部分
奥斯卡颁奖大典最近几年添了一项内容:将年内去世的电影名流(演员、剧作者、制片、导演)生前作品片段,辑录集锦现场播映,名曰“怀念”。在连绵起伏的配乐中,亡者名姓连串而过,这时,盛会的喜庆气氛倒也不是乐极生悲,却陡然伤感起来。人死了,角色仍在银幕上哭笑,且大抵是早期黑白电影里的俏姑娘或俊小伙,鲜蹦活跳。其实当代的观众早已忘了吧,忽然重逢,啊,是他(她)们呀!
第四部分
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将电报扔进废纸篓。事在1946年。但他与吉洛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还没完。以下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页―214页:我提醒他,马莱伯曾指出,对国家来说,一个诗人的作用还抵不上一个成天玩九拄戏的人。
第五部分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琐记_《纽约琐记》 -参考资料
http://book.qq.com/s/book/0/11/11694/index.shtml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