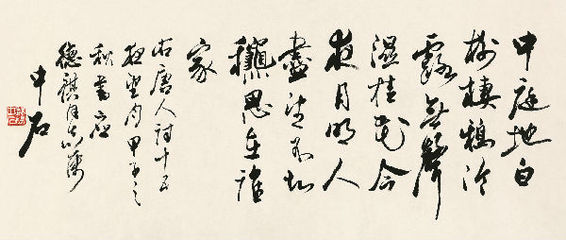胡思杜(1921―1957),胡适先生幼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194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1957年“反右”期间,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胡思杜_胡思杜 -死亡揭秘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
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竹圭(应为三个“土”)生,但竹向胡适反映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
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思杜。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
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胡适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骨肉,对此,大陆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邓广铭先生就如此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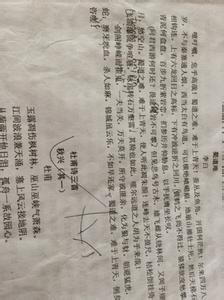
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胡适日后的日志中看到些蛛丝马迹来:“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检(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他去年四日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自己‘坦白’!”(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
同时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胡适进行统战,希望胡适为新政权服务,但都被胡适所拒绝了,这也就是杨金荣先生所说的胡适“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此时,表示要作政府“诤臣”的胡适已经被国民政府以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身份派往了美国,寻求援助。胡适刚到美国不久,中共的《人民日报》和香港共产党所控制的左派报纸很快先后登出了一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统战意向十分鲜明”。胡适经过分析,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并于1950年1月9日写了《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后更名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逐条予以分析驳斥。有趣的是,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在两天(即1月7日)前,他刚刚收到徐大春寄来朱光潜在大陆的“自我检讨”。
争取胡适失败后,中共在大陆便开始酝酿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序幕最终决定由思杜来揭开。9月22日,思杜在左翼控制的《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但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则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中央日报》于9月29日刊登了傅的来信。傅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胡适事后则进一步“醒悟”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同上)
关于胡适为何“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不同流派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只能摘段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或许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猜测到胡适的一些真实想法吧:“胡适之也是反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着,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思杜因此次的“表现”受了中共的表扬,“学习改造”结束后,思杜还到堂舅家取走了那一皮箱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
随后,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有对象他也许就不会死了。”
接下来的几年,倒也似乎风平浪静,关于思杜的线索几乎“中断”了,直到1957年反右。在这期间,胡适除了收到过几封从大陆发来的信件,还被告知大陆发生了一宗“疑案”:“香港胡中正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思猷是二哥绍之的儿子,大夏大学毕业……”(胡适1950年11月11日日记)
只是胡适至死也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会在七年之后发生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据思杜的亲人胡恒立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我们可知:“反‘右’之前,共产党自上而下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杜不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预示,他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绝望而自杀。”
思杜是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的,其所在单位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人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思杜同一个系的共产党员同事告诉胡思孟,思杜在事先把自杀的原因都告诉他了,他死前还给思孟留了个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他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胡思孟表示要带走“遗书”,但“他的单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给我抄了一份。”此时的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思杜的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迫离开了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胡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
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最后,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遗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独子胡复。
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思杜_胡思杜 -注释
沈卫威着《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下简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8页
邓广铭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0页
摘自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全18册)第16册(1948.1-1950.12),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17日初版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9页
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215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文化》第152页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次印刷,第24-25页
江泽涵夫妇于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1页
胡思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沈卫威的谈话,摘自《文化》第154-155页
《文化》第155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