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李文旺
母亲是个劳碌命。她虽然比奶奶幸运得多,奶奶四十二岁就中年守寡,带着四个孩子――――――三男一女过活。可是,奶奶遇上了解放,遇上了共产党,特别是父亲和大叔、二叔这三个孩子都成年了,二叔又当上了小学校长,以前送给人家的女儿通过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竟然找到了。所以,在我小的时候,过惯了苦日子的奶奶不但没有喊过苦,而且总是乐乐呵呵的。再说,奶奶的孙子辈太多,对于奶奶的艰苦我也知道得很少。可是母亲就不同了,虽然养了生了七个孩子,两个夭折,活下来五个孩子,其实只有四个。那是因为:母亲在1956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送给了同村的干部,因为这个村干部是我父亲和二叔的救命恩人。
说起这事,还真有一段故事呢。
1956年,虽然还不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可是,国家刚刚从内战的局面中走来,加上抗美援朝战争,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虽然在潘村还没有逃荒的人,但是大家几乎穷到要吃米糠伴稀饭的地步。在一片湖水茫茫、大大圆形的琵琶湖里,多的倒是吃不完的鱼。潘村的人们每次下湖捕鱼,最少也能捕获个二三十斤鱼。有一次,我母亲将父亲潘万里从琵琶湖打来的三十多斤鱼从一个大大的竹篓子里倒出来,捡出杂草和死鱼。然后再将这些鱼装进篓子,她让潘万里拿到离家只有二十米的琵琶河里去汰一汰。琵琶河是一条绕着琵琶湖的弧形河流。琵琶湖和琵琶河之间那些略微高些的地方,就是赤岗区(人民公社化以后,赤岗区后来改成赤岗人民公社)人民赖以生活的地方。潘万里来到河边,踩着一块大大的石头蹲在河边,他不断地摆动着那大大的竹篓子,好让每一面都让河水冲洗得到。也许是潘万里做事一向马马虎虎,他踩着的居然是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他脚底下一滑,连人带篓子滑到河里。琵琶河虽然到了这儿是绕着琵琶湖的,但是它又是信江的一条支流,从上游的三十里处就被称为琵琶河,这条河又长又深,也许是因为其长才有其深吧。一般不会水的人要是落入琵琶河里,那会是九死一生的。
在不远处干活的潘万强――――潘万里的弟弟,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不轻,他看见哥哥掉到了河里,飞快地跑过来,连衣服也来不及脱下,就迅速地跳到河里。可是,潘万强虽然比他哥哥的水性好些。但是,他对于游泳也最多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不但没有把他哥哥救上来,兄弟两个抱在一起在河里不断地扑腾、挣扎。这时候,划着船准备去十里外的草洲上割草的潘富贵看见了――――――割草沤稻田是赤岗区人长期的老传统。他迅速地将船向潘万里兄弟靠拢,等到船靠近了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马上伸出长长的竹篙,让潘万里潘万强兄弟抓住。潘万强到底年轻些,很快就爬上了船,可是,抓住了竹篙的潘万里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还是爬不上船来。是啊,潘万里一大早出去打渔,回来时候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来到河边汰这鱼篓子。就算是要吃早饭,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锅里倒是有半锅白水煮草鱼,寡淡无味的鱼也是很难吃的。空着肚子的潘万里在水里又费尽了力气,此刻凭着他自己,连爬上船的力气也没有了。看着精疲力竭的潘万里,潘富贵很快地跳到河里,使劲把潘万里托起来,把他从河里推到船上。就这样,潘富贵成了潘万里兄弟的救命恩人。可是,潘富贵做好事,竟然成了又一个雷锋――――――命运怎么就那么对他不好呢。潘富贵两夫妻结婚十年都没有生下一个孩子,我父母为了报恩,将双胞胎中的一个送给了村干部潘富贵。好在那双胞胎都还只有两个月大,不然,孩子要送人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孩子认生啊。这样,母亲就只有四个孩子了。( 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是啊,潘富贵是个好人啊,他不但救起了潘万里和潘万强兄弟两个,在船上,他刚刚救起了潘万里,也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可是,他顾不上喘口气,就对潘万强说:你那样救人不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救,至少你得抓住对方的头发。
这样看,母亲还真是个苦命。母亲在1956年生下双胞胎,本来也是不错的事情,农村的女娃子好养,那时候,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至少潘万里是这思想。女娃子可以不让她读书,到了十来岁就可以让她放牛挣工分,好歹可以养活自己。可是,母亲刚刚生下双胞胎,就欠人家人情,欠人情还不说,还是欠一个同样命薄人的人情。最后,居然要拿自己的孩子还人家的情。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少见的。
呵,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母亲的名字呢。母亲叫何牡丹,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让我更好的记住普通母亲的这个并不普通的名字,就允许我通篇都用何牡丹的名义吧。
我们家乡的环境应该交代一下。
我生长在潘村――――――赤岗公社琵琶州大队潘村,是个彻头彻尾的水乡,1974年,潘村有农户七十户,在这周围十里八乡是个中等村庄。在赤岗公社,大的村子有一千户挂零,那是一个叫做吴泥的村子,全村的人几乎都姓吴,这个村有一个在大跃进时候考取清华大学的青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已经一步步地上升为武汉市市长了。当然,在琵琶州村的周围,也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潘村据说是从福建省惠安迁移而来的。十六世纪初期的中国,倭寇在东南沿海十分猖獗,惠安处在东南沿海的前沿,当地人民深受倭寇的欺凌。惠安有一潘姓人家,是个大家庭,有八口人。这一家八口为了逃避倭寇,一路北上,到达赤岗这个地方。在这里,人烟稀少,有一条绵延十几里地的河流,河流的中段有一个很大的湖面,像一个偌大的葫芦挂在这段河流的腰间。这一户人家也不知道这地方好不好,暂且在这里盖了一处简易住所,打渔为生。初夏的某一天,这家人家的第二个儿子打完鱼回家,遇见一个风水先生,于是他们聊了起来。风水先生告诉他:这里可以发三百户。这潘家老二不信,风水先生让他在河边倒插两棵樟树,并言之凿凿地说,如果这两棵樟树活了,你就在这里安家,如果是樟树死了,你就离开这里。第二年,樟树真的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时代相传。
赤岗公社离中国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很近,和庐山隔湖相望。赤岗公社本身也是一个小小的圆形湖区,那个湖面被称为琵琶湖,当然这个湖区只是一个浅浅的水荡,因为这个水荡的浅而平,与其说赤岗公社的这个水荡是个充满水的盆地,倒不如说这水荡更像一个碟子,只是中部稍微低洼些而已。所谓赤岗公社里有一个“岗”字,容易让人联想起山地和石头,其实,除了赤岗公社所在地只有一块起伏也只有三米高的石头山之外,在赤岗公社实在很难找到硬硬的土地。况且那片海拔三米高的石头山,其范围也只有一千八百平方米,如果要说石头资源,实在是会让山区的人们笑死的。
任何资源都是有优势同时有其劣势的,虽然赤岗公社其实根本没有石头可以开采,但是,这地方实在可以称之为土地肥沃,沃野几十里,完全可以成为“十里荷塘,二十里鱼塘”标准水乡。
赤岗公社的八个大队就围绕这这个碟子或进或出地沿着碟子的最边缘分布。他们共同耕作着琵琶湖这一片大约一万五千亩的水田。所以说它是水田,和说它是水稻田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早在六十年代,因为人口和人力的稀少,碟子的中央长期都是被水面所淹,那时候的水利电力各方面工作也不发达,加上劳动力稀少,大家面对着长期被淹的湖面只能是任其自然,或许那时候的赤岗公社的中心部位也不是什么被淹,它原来就是一片野生鱼自由活动的天然渔区,所以,在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赤岗公社的社员长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吃不完的鱼,吃不饱的饭,以至于后来的六零后七零后竟然会误以为他们的祖辈过得都是天堂般的生活――――――有鱼吃多好,都说鱼肉百姓鱼肉百姓,没有谁说“萝卜百姓”或者“白菜百姓“的;过年的时候,人们最满足的除了有肥肥的鸡以外,另外最稀罕的东西就是肉和鱼了,可见鱼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时候,他们的祖辈就会哭笑不得地告诉他们说:“孩子啊,你们不懂啊,在赤岗公社,有个顺口溜说:“吃鱼没有油和盐,过年没有一元钱,万恶世界不砸烂,何来一片朗朗天。”
在琵琶湖这一万五千亩的水面和土地上,在解放初期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用来种水稻的面积只有五千来亩,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才慢慢将湖区中央的水面逐步规划。怎么规划呢?公社用拦堤作坝,在堤坝上建起了排灌站,排灌站里安排这几个硕大的排灌工具――――――抽水机,那些抽水机可真够大啊,它们的管子竟然能钻过去肥大的水牛还绰绰有余。大马力的抽水机将琵琶湖中央大量的积水排干之后,周围几个大队的社员硬是用锄头将这些积满淤泥的湖面变成良田的。
如果在琵琶湖这个圆上画一条直径线段,那么琵琶湖大队和赤岗公社正好在这条直径的两个段点,因为琵琶湖的稻田成片,并没有一条直通赤岗公社的大道,所以,琵琶州大队和赤岗公社只能在琵琶湖这个大圆上遥遥相望。所以,琵琶州大队的干部开会,学生读高中,群众交粮食等等等等的事务,全部要经过这个圆上那弯弯的弧形道路。
在琵琶湖,自古以来,人们不怕干旱,可是,最怕的就是下雨,因为一下雨,就要担心涨水,一涨水,稻田里就要颗粒无收。所以,在琵琶湖,人们常常念叨的是“大涝三六九,小涝年年有”,自从有了赤岗排涝站,琵琶湖的人民抗拒洪涝灾害的能力明显提高。自从1954年的大洪涝以后,再也没有过那么大的灾害了。但是,在琵琶湖这一带,一个流传于少年儿童的童谣可谓历史悠久。童谣说:“天老爷,别下雨,让我给你捏玩具, 捏一个天仙让你娶,捏一个张飞骑毛驴,捏一个关公长胡须”。
是啊,为了祈祷少下一些雨,人们竟然连作为门神的关公关老爷都想到了。
可是,天要下雨,就如同那什么,嘿,其实那什么还不是和天要下雨似的?所以,天要下雨是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不,1966年的梅雨季节,一个炸雷将那个村干部潘富贵和他的妻子打死了。唉,好人怎么就这么不长命呢?
何牡丹那个双胞胎女儿因为得了麻疹,在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个送个潘富贵的女儿――――――潘美丽就又回到了何牡丹的身边。
在潘美丽回到亲生父母潘万里和何牡丹的身边这件事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潘富贵的弟弟潘宝贵家,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孩子,他就是潘宝贵的儿子潘七彩。也许是童年的潘美丽常常逗着两三岁的孩子潘七彩玩,以至于后来已经是五岁孩子的潘七彩哭着喊着不让何牡丹把潘美丽要回去。何牡丹觉得潘七彩怪可怜的,也就不再强求要带潘美丽回去,而是客气地征询潘宝贵的意见。何牡丹说:“潘美丽虽然是我生的,也不是我不喜欢她,我们倒是很想带她回来,可是,她毕竟跟着你哥哥潘富贵过了十年,你也就是他的亲叔叔了,想不到潘富贵,哦,不,想不到潘队长突然死了,那,如果你愿意将潘美丽收养作为女儿,我什么话也没有。”
其实,潘宝贵是最不愿意收养女孩的,为什么?他自己家就有三个女儿,他现在只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他缺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虽然,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夭折,可那毕竟是后话。
潘万里是村干部潘富贵救下来的啊,所以,潘万里和何牡丹都为这个救命恩人的死难过。在潘村,对于潘富贵的死,大都说是好人不长命,可是,村里马上又有人说,这潘富贵其实是很不地道的人,是个流氓,仗着他当过志愿军,还到前线打过几次已经没有什么风险的仗,加上在村里救过人,所以,常常以救世主的面孔出现;年轻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可是,近两年来,时不时地勾引村里的少妇。于是,又有人添油加醋地回忆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潘富贵还偷了集体很多粮食。这事也就是这么说说,其实谁也没有具体的证据。
因为潘富贵夫妇是在为生产队出工的时候被雷电打死的,所以,琵琶洲大队要为潘富贵申请烈士。可是,因为村里有不少不好的反应,所以,申请烈士的事情也就搁下来了。有人说,就算是潘富贵一向表现很好,可出工的时候被雷电打死,又不是在为村里干活的时候打死的,补助点抚恤金就不错了,有什么必要申请烈士啊。公社和县上一考虑,觉得说这话也有道理。
但是,县上委托赤岗公社说,好歹潘富贵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又当过十几年村里的头头,除了抚恤金以外,应该对他的亲属照顾一点。公社报告说,潘富贵原来收养的女儿已经还给了潘万里,不过,潘富贵还有个弟弟,叫潘宝贵。县上明确表态说:那就照顾照顾那个潘宝贵,怎么着也得让他当个干部什么的。赤岗公社向县上报告说:经过了解,那个潘宝贵没有文化,县里问:他多少文化啊?公社说:他读了两年书,差不多就是个文盲。县上有些不高兴地说:怎么回事,你们赤岗公社落实一点这样的指示都那么支支吾吾的,人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没有评上烈士就已经有些冤屈了,难道照顾一下他的亲属还不应该吗?再说了,我们的基层干部,哪一个是有多少文化的,再说,这潘宝贵不是还读了两年书吗,怎么能说他是文盲啊?
其实公社本来是想反映一下潘宝贵不太好的本质的,可是,听着县上的训斥,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于是,这个本质并不好的潘宝贵竟然接上了他哥哥潘富贵的班――――――当上了潘村的生产队长。
潘宝贵是个幸运儿,要是再晚三个月,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这样的人也是当不上村里干部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就像一把火,没有什么错误的老资格的干部都常常被烧成了光屁股,何况像潘宝贵这样一身毛病的人呢。
潘宝贵当上村里的生产队长以后,真本事没有,可是迎合文化大革命的风向倒是十分机灵,他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除了见风使舵,他还是一个心胸极为狭小的人。1967年,何牡丹的大儿子潘小荣想当兵,可是,潘宝贵竟然以潘美丽被潘万里要回来为借口,公开阻拦潘小荣当兵。
其实,潘宝贵和潘万里的矛盾远远不止这些。那得从头说来。
1950年,潘村只有三十户人家,那时候,潘村的人住在离开现在潘村五百米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到处都是一片洪水,那个地方相对要高不少,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因为接连半个月的雨天,琵琶湖到处都是一片洪涝,潘村的许多壮劳力都去十几里地之外的地方抗洪去了。在潘村,除了生病发着烧的潘万里,村里就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孩子。那一天,潘万里几乎一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潘万里和潘宝贵家是隔壁。 突然,一把大火隔壁的潘宝贵家的房子给烧着了,当潘万里看见隔壁的火光时,火苗已经不小了,他忽地一下窜起来,迅速拿起水桶跑过来救火。那个老得不识大体的老妪吓得够呛,她最先做的事情不是去救火,而是忙于抢救她家的东西。气得潘万里一把将她推倒一边去了,老太太慢慢爬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因为那时候住得密集,而且三十户人家全是木房。这一把火蔓延开来之后,来了个火烧连营,三十户人家烧了个精光。据潘万里分析,这把火是这个老妪烧饭时候惹下的。这七十岁的老人耳朵倒是很好,可是,眼睛有些毛病,看东西很是模糊,一不小心,在灶房里就把火给点着了。
烧的已经烧了,再怎么诅咒也挽回不了损失,潘万里只好如实和从远处赶回来救火的人说:火是从潘宝贵家烧着的。考虑到和潘老妪毕竟是多年的邻居,他没有把潘老妪不去救火而去救她自己家东西的事情告诉大家。按理说,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再说,当时推了潘老妪一把也没有把她推得怎么样。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之后,老太太死了。其实,在1950年,像潘老太太活到七十岁的寿命已经是不错的了,古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太太已经过了古稀了。可是,两个月前,老太太就把潘万里推她一把的事情告诉了潘宝贵。回过头来说,如果真的推出什么毛病来,一来等不到两个月,二来,当时潘宝贵也完全可以找潘万里算账。可是,他没有。潘宝贵也没有把潘万里推了老妪的事情告诉他的哥哥潘富贵,只是心里狠狠地记下了这件事。
潘老妪的死让潘宝贵把这笔账记到潘万里的头上去了。就在他哥哥潘富贵救潘万里兄弟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在心里责怪他哥哥糊涂,心想:潘万里是他们家的仇人啊,至少不是什么好人,干嘛还去救这样的人啊。可是,救人的事情,既然发生了,总不能把救起来的人再次推到河里去吧。所以,潘宝贵干脆把自己对潘万里的仇恨隐藏着。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潘富贵就这样死于雷电。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对于潘宝贵阻拦潘小荣当兵的事,潘万里想起潘宝贵的哥哥救过他,也只好忍气吞声了。
可是,潘万里的忍气吞声,却让潘宝贵更加嚣张。自从1968年开始,潘宝贵当上了潘村生产队长,可是,这个队长在刚刚当上生产队长的时候便是个甩手掌柜,喜欢对着社员吆五喝六的,不但脾气大,还很少参加生产劳动,今天去公社开会,明天去县上开会,要不就是窝在生产队队部和村里的会计搞什么季度结算、年中结算、年终结算。一年到头参加真正下地干活的时间不超过四十天。所以,有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说:“生产队长真不亏,东游西逛好(hao读第四声)指挥,好在社员真自觉,不然生产全化灰。”
潘富贵还是很会来事的,他很能笼络人心,所以,几个得到他照顾的社员,或者是他的亲戚,对他不但不反感,还服服帖帖。在潘村,潘富贵的同一家族的人就达四分之一,加上他笼络的人,这样算下来,潘富贵虽然游手好闲,坐镇指挥,可是,他照样能让社员们为他挥汗大干。
到1968年,潘小荣再次积极报名参军,可是,潘宝贵竟然又一次阻拦潘万里的大儿子潘小荣当兵,这一次的理由是,潘小荣的脚是内八字。这一次,把潘小荣给气坏了,他恨不得要和潘宝贵拼命。是何牡丹极力拦住了儿子,何牡丹几乎要给儿子下跪了,潘小荣才没有找潘宝贵的麻烦。
好在参与县上新兵体检的部队一个军官看上了潘小荣,直接点名要潘小荣,这样,潘宝贵的阻拦才彻底失败。
让所有潘村人不解的是,在欢送潘小荣入伍的队伍中,潘宝贵这个队长竟然成了较为热情的一个。
潘小荣十分不解,他问何牡丹:“妈,这个人怎么还有脸给我送行啊。”何牡丹说:“儿子,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既然改了,我们还和人家计较什么啊?孩子,记住,一个没有度量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这样,潘小荣才没有和潘宝贵过不去。
1968年的春天,潘万里和何牡丹将儿子送到县上,县上新兵更多了,那气氛,那热闹劲儿,是大队和公社无法比的。县城的大街上贴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英勇杀敌,保卫国防”等等鲜红的标语。全县五十八个新兵现在都到武装部去了,说是要换好军装再到县工会的篮球场聚集的。县工会右边停着几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据说那就是运送新兵的汽车。工会的左边有个照相馆,那也是全县最大的照相馆。何牡丹看着县城那一番热闹的景象,再看看那几辆新汽车,觉得自己为国家送了一个新兵,内心里充满无限的光荣和自豪。
潘万里和何牡丹、小儿子潘小冬在照相馆门口等着和潘小荣照相。是啊,如果和穿上解放军新衣服的儿子合一张影,那该是多美的事情啊,虽然照一张合影要四毛钱,让有些人心疼那钱,可是,在何牡丹看来,就是花两元钱,不,就是花上再多的钱,也应该和当兵的儿子合影啊。此刻,何牡丹多么想儿子很快出现在自己的身边啊。
过了一袋烟的功夫,已经是全副军人打扮的潘小荣出现在何牡丹的眼前。何牡丹双手挽着潘小荣的臂膀,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花。是啊,能不激动吗?儿子能穿上崭新草绿色的军衣,戴上亮闪闪的红五星,似乎格外帅气。家乡是血吸虫病灾区,不要说当兵,以前多少人根本就没有想过当兵的事情,他们的最大理想就是不要得上血吸虫病。何牡丹深情地看着儿子,她用手去摸潘小荣的脸,潘小荣看着周围那么多同龄人,他们都穿着是军人打扮,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推开了何牡丹的手。何牡丹知道他害羞,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潘万里一个劲地给潘小荣随身带着的军人挎包里塞熟鸡蛋,还不到四岁的潘小冬吵着要吃鸡蛋。何牡丹把潘小冬领到旁边,她哄着说话都还不太利落的潘小冬说:“孩子,那鸡蛋是给你哥哥路上吃的。我回头再给你买两个,好不好?”这样,潘小冬才不吵了。
何牡丹给潘小荣整了整衣领,深情地说:“儿啊,你这一走,可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家除了我、你爹还有你,可就是老的老,小的小了,你奶奶都七十四了,还说一定要到县上来送送你,让我给拦住了。可你奶奶那份心情可不敢忘记啊。你可要在部队上好好干啊,给我们,不,给我们潘村增光啊。”潘小荣说:“娘,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表现的。”
何牡丹又说:“到了部队,可要记着听部队领导的话,你听领导的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因为毛主席管着你们部队领导呢。”潘小荣说:“妈,我记住了。”潘小荣多么想他的父亲潘万里说些什么,可是,潘万里几乎是个闷葫芦,很少开腔。何牡丹又说:“孩子,到了部队,不要爱惜力气,多干点,也累不到哪里去,人的力气就像海绵,你要挤,它总是会有的。不过,你除了多干活,也要注意身体。”何牡丹这样翻来覆去地说着,潘小荣总觉得她的话有些唠叨,可是,他知道妈是为了他好,他也就让她唠叨,自己多听些,到了部队恐怕还听不着呢。
何牡丹突然想起了这几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吃紧,广播里常常说“苏修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她又有些担心起儿子的安全来了。可是,当着部队首长的面,她又不好说出自己的担心,唉,要是说出自己担心儿子的安全,人家首长该怎样看待自己啊。是啊,当兵不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然,国家花那么大的代价养着这么多兵干嘛!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国家养着军队,而军队什么活也不干,什么危险也不冒,军队还提什么保家卫国啊,就是那些工程兵、通信兵等等其他兵种的军人,归根结底还是为保卫国防服务的。何牡丹把快要说出口的话又咽回去了,参加接兵的部队首长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说:“大嫂,你放心吧,你儿子一看就是个好兵,不用挂念。”何牡丹也不愿意耽误首长的时间,和他们挥了挥手,就领着潘小荣往照相馆里走,四个人一边登着照相馆那木制的楼梯,何牡丹一边叮嘱说:“儿啊,你得记住,记着给家里写信啊。”有道是:“儿想娘一阵子,娘想儿一辈子”,何牡丹此刻似乎要把几年的话一股脑儿对着儿子一口气说完。
照相馆里的师傅手里捏着一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让何牡丹一家四个人笑一笑,然后,咔嚓一声,师傅说:“好了,你们的全家福照好了。”何牡丹说:“师傅啊,也算是,不过,我们家还有两个女孩子没有来呢。要是加上她们,那才是真正的全家福呢。”
望着徐徐开动的汽车,何牡丹挥手和潘小荣告别,她忍不住热泪往下流。汽车在何牡丹模糊的视线里离开了,何牡丹的心似乎被挖去了一点什么似的。送走了潘小荣,何牡丹有些怅然若失,她和潘万里、潘小冬一起,默默地回到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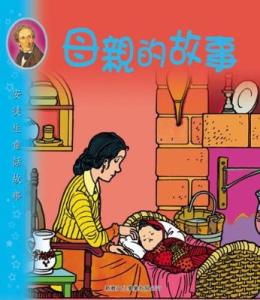
当天傍晚,何牡丹看见女儿潘美丽手里拿着一朵红花反复摩挲着,对六岁的妹妹潘美君说:“妹妹,你看这朵花漂亮吧。”潘美君伸手想要那朵花,潘美丽说:“让你玩一分钟,我数着数儿。”潘美丽算着六十秒,很快又将红花要了回去。是啊,她多么喜欢这朵花儿啊,尽管它只是一朵纸做的花,可是,在潘美丽看来,比真正的鲜花还要珍贵。她一会儿把红花放在手里抚摸一番,一会儿又把它别在胸前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偷偷地笑着。她想孩子一定是很喜欢这朵花,可不要打扰女儿,让她高兴去吧。是啊,女儿早就到了读书的年纪,可是,因为潘万里的反对,在潘美丽最好读书的年纪,竟然一直在村里放牛。何牡丹心里都总觉得过意不去,现在,女儿这偷着乐的一点秘密可不要打断啊。
晚上,潘美丽刚刚睡下,她将那朵红花放在枕头边,竟然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她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了。在梦里,她高兴得笑了起来。第二天,何牡丹看着醒来的潘美丽,她拿起枕头边的红花,问:“孩子,你这朵花是哪里来的?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潘美丽说:“妈,这是我昨天捡到的。昨天我偷偷地到了县上,我怕你们赶我回来,所以我没有让你们看见。这朵花,就是我在工会球场上捡到的,是一个当兵的丢下的。”何牡丹说:“孩子,你才多大啊,就敢自己一个人到县城去?!”潘美丽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啊,到县城不就是五公里路吗?我到姑姑家都走过四五次了,她家就在县城的南边,才一里地呢。”何牡丹还是不放心地说:“下次可千万不要这样啊。走丢了怎么办啊?”潘美丽说:“妈,你也太小看我了,我都十二岁了,不,我虚岁都十三了呢。”何牡丹没有想到,好像一夜之间,潘美丽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不但敢于一个人敢于到五公里外的县城玩,还能说会道了。可是,她不明白,女儿要这朵红花干嘛。何牡丹问:“你要这花干什么啊?”潘美丽答非所问地说:“妈妈,我要读书,你就让我读书吧,要是读了书,我也可以和哥哥一样去当兵。”何牡丹说:“那你得去问你爹,家里的大事情是你爹做主的。”潘美丽说:“不,不嘛,我知道,爹是个旧脑子,他还不如你开通呢。”何牡丹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说你爹呢?”潘美丽说:“就是,就是嘛,这三年来,加起来有六个学期吧,那一天我不盼望着读书啊,可是,我年年都要求读书,爹就是不答应,说女孩子是不用读书的。这不,我现在都十二岁了,还读不上书。你再看看二叔的女儿,只是比我大三岁,她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何牡丹说:“孩子,你是说潘美晨吧?你啊,怎么能和二叔的女儿比啊,你二叔当着校长呢,也算是个文化人啊,二叔两个儿子都还小,他家最大的孩子也就是这个女儿了。”潘美丽说:“二叔的女儿可以读书,我为什么不可以读书?哥哥都读了初中毕业了,我一天书也没有读,这太不公平了。”何牡丹说:“孩子,你怎么能说一天书都没有读呢,你不是还读了三年夜校吗?” 潘美丽说:“夜校根本就不能和全日制的相比了,对了,妈,你不说我还忘记了呢,是的,我读过三年夜校,老师常常说我读书不错,我这三年夜校啊,可以和全日制二年级的学生比。”何牡丹说:“说什么呢,你那个夜校我还不知道吗?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两头都缺少老师,你怎么能和二年级的学生比呢?”潘美丽说:“就是就是,妈,我不骗你的,我真的可以和二年级的人比了,不信,我带你去问我那个夜校老师吧。”何牡丹让潘美丽缠得没办法,干脆连连点头说:“好了好了,我信,我信。”潘美丽说:“那么说,我求求你了,让我读书吧,我可以直接读三年级,省去读一、二年级的时间,等我长大了,我,我……”潘美丽的眼里竟然含着些泪花,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激动的。
何牡丹看着女儿那认真而又稚气的样子,心里既觉得好笑,又不免难过。是啊,何牡丹其实也觉得女儿读书是应该的事情,可是,她几次和潘万里商量过,得到的答复总是:“女孩子迟早要嫁人,还不如让她多增挣一些工分。”其实,潘万里还有一个更加封建的思想:他觉得这潘美丽送给人家做了几年女儿,多少都有些疏远了,他不想送一个已经疏远了的孩子读书,接下来,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呢。儿子就是昨天那个还在妈妈的怀抱了的四岁孩子潘小冬,女儿就是出生于1962年的潘美花。
现在,女儿潘美丽决意读书,何牡丹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虽然何牡丹是一个农村的妇女,而且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妇女,她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在她心里,其实,男孩和女孩是完全一样的。既然潘美丽提出要读书的事情,她 再也不能听从潘万里的安排,她打算和丈夫潘万里据理力争了。她想,自己就是负担再重,也无论如何要争取让女儿潘美丽下半年读上书。可是,争论的结果是,潘万里死活不同意让女儿读书。
一个多月后,正是端午节的时候,潘万里收到了儿子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书信,何牡丹高兴得什么似的,他催着潘万里读给她听听。潘万里说:“我还不是和你一样,这信上的字认识我,可惜我不认识它啊。”何牡丹说:“我光顾了高兴了,忘记了你也是个睁眼瞎了。那还是把女儿找来。”潘万里想:潘美丽只读过夜校,哪能念信啊,还不如把他二叔的女儿潘美晨喊来,她现在已经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他说:“还是把潘美晨喊来吧。”何牡丹说:“喊什么喊,美晨这几天天天都在参加那个什么活动,哦,对了,说是造反派要选几个初中生跳忠字舞,结果把她给选上了。”潘万里说:“作孽啊,她,就她,她潘美晨才多大的人啊,也要去跳这舞啊。”何牡丹嘘了一声,说:“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可没有好果子吃啊。你可别看潘美晨年纪不大,可是个头大啊,有的高女生都不如她高大。”潘万里说:“那倒也是。唉,真是笑话,这都解放了快二十年了,找一个会念信的人都这么困难。唉。”何牡丹有点不耐烦地说:“你左一个唉,右一个唉,一个大男人整天叹什么气啊,像你这样,再好的日子也让你给说倒霉了。人啊有点困难怕什么,你还记得不?那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多困难啊,不也过来了;还有,政府造原子弹,苏联人想看我们的笑话,不也没有看成吗?我们不是也很快就搞出了原子弹吗?”潘万里说:“去去去,原子弹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何牡丹气闷得不行,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虽然不抽烟不喝酒,可是也说不上勤快,不勤快倒也没有什么,可是,说起话来竟然这样一塌糊涂,真是个死脑筋,也难怪潘美丽会责怪他这个当爹的。是啊,就这么个男人,当初能够答应他的婚事也是看着他忠厚老实,加上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可是,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糊涂虫,何牡丹是不会嫁给他的。
这时候,到琵琶湖的水沟里抓鱼的潘美丽回来了,她看见何牡丹手里拿着一封信,故意假装没有看见。何牡丹抱着试试看想法说:“孩子,你哥哥来信了,你快给我们念念吧。”
潘美丽仍然想着父亲不答应她读书的事情,她还在和潘万里赌气,把嘴唇撅得很高说:“妈,你可别怪我,有人不让我读书,可我就是命贱,还给家里抓鱼,看,这一大篓子鱼可都是我抓来的,起码得有五六斤吧,可要说念信,对不起,妈,我没有读过书,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潘万里知道这女儿也是个倔脾气,她明明在夜校读书是最好的,可竟然说一个字也不认识。这点鱼算什么,其实她平时要是一出马,那次不是能抓回来七八斤鱼啊,今天这才五六斤鱼,还在这儿说嘴,还拿着抓鱼来做挡箭牌,唉,这女儿到底还是不是亲生的啊,难道那几年送给人家收养,她一直记着他潘万里的错儿吗?
潘万里此刻有些后悔,当初把刚刚出生的女儿送人还真有些对不起她。不管收养她的人对自己有多大的恩情,也不能拿亲生骨肉做交易啊,也难怪女儿赌气。潘万里听着潘美丽的话,也不能发作,此刻甚至还有一点懊悔。看看,现在不但来信没有人念给他们听,就是女儿那副成天板起来的脸也够让人难受的。
潘美丽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她看见潘万里那蔫头耷脑的样子,知道自己要是再进攻一番,向潘万里提出读书的要求,也许他不会死死地卡着不放,毕竟自己是他最大的女儿啊。
潘美丽说:“爹,你要是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不但可以念这封信,还可以把家务事都包下来,给你们读信就更应该了。”这一声“爹”让潘万里心头一热,因为读书的事情,她和潘万里闹了好久的别扭,潘美丽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喊他爹了。潘万里原来只是以为女儿读书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个丫头读书的愿望竟然这么强烈。他开始犹豫了,虽然现在潘村读书的女孩子只有两个人,可是,像潘美丽这样强烈要求读书的人也实在很少,再坚硬的心肠也会然潘美丽那诚挚的要求所感动。不用问,潘美丽的条件一定是要读书。
潘万里为了试试潘美丽,故意问她:“说说看,孩子,你的条件是什么?”潘美丽也毫不掩饰说:“爹,你让我读书,好不好?只要你答应让我读书,我马上给你读这封信。以后的信我也全部给你念。”潘万里此刻已经让潘美丽执着的好学精神所打动,但是,为了进一步考验一下潘美丽,他故意又提起以前对潘美丽说过的话:“孩子,我们这儿的老辈人说过,女娃子,不认字,嫁了老公过日子,传宗接代生孩子。”这话,以前潘美丽听不懂,现在,她已经是豆蔻年华了,她害羞得忙低下头去,用双手捂住耳朵说:“不听,我不听。”看着女儿那害羞得样子,潘万里觉得自己这个做爹的已经有些过分,是啊。虽然潘美丽送给潘富贵收养了好几年,可是她不还是自己的骨血吗,干嘛要另眼相看呢。再说,放牛的日子她也已经过了好几年,再不让她读书,她则会一辈子就和上一代人一样,也是个睁眼瞎了。
看着潘美丽那稚气未脱的脸,潘万里深情朝她点了点头说:“好,美丽,爹答应你,爹决定到下半年就让你读书了,至于你给生产队放的牛,我会和队长说明情况的,到时候自然有其他的人接替你的,我们村,有些女娃子还担心捞不到放牛的事情呢,毕竟那也是一份差事啊,可以顶二分的工分呢。”这时候,一颗大滴的眼泪从潘美丽的眼眶里夺眶而出。她顾不得害羞,用力地抱着何牡丹不放,使劲地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何牡丹高兴坏了,她笑哈哈地说:“是你爹同意你读书的,你干嘛不去亲亲你爹啊?”潘美丽害羞地说:“他是男的。”何牡丹笑得更厉害了:“哈哈哈,你个傻闺女,什么男的女的,那是你爹啊!”
潘美丽到底是个聪明的孩子,满满两大张信纸的内容,她很轻松地就读完了,看她那架势,根本不是只读过夜校的人。当然也有两个读不来的字,只是两个。一个是“手舞足蹈”的蹈字,一个是“温馨”的馨字。
潘小荣的来信说:“这一个月来,除了基本的军人队列、射击动作等基本知识以为,他们这批新兵的胆子也大了不少,因为,潘小荣现在知道,天下没有什么是可怕的东西。近期,部队里进行了夜间寻物综合训练,那既训练胆魄又能训练智慧。因为这封信写得很详细,以至于潘美丽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手舞足蹈,读得绘声绘色。儿子潘小荣说:这项训练,是在夜间把目标物件藏在部队驻地十里之外的某一个地方,让新兵一个个去取回。好在部队领导将这些东西说明了大致的方位。可是,仍然有不少新兵吓得半路往回跑。因为快要到达目标的地方竟然有几座坟地。可是,潘小荣仍然坚持向前,在快要找到目标物的时候,坟地已经不是星星点点了,而是连成一片了。当时,潘美丽也想打道回府,因为那些坟墓不但杂草丛生,有的坟墓居然还能看见被盗墓者挖开的口子。这时候,就连几个胆大的新兵也不敢往前走了。结果,全连一百多新兵,分十次进行夜间寻物训练,最后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的新兵竟然不到十个人。”信里,潘小荣还说,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任务,和母亲送别他的时候那一番温馨的鼓励有很大关系。
听了女儿读信,潘万里抛弃了他固执的思想,觉得这几年没有让女儿读书真是有些可惜,也错过她读书的好机会。
又过了一个月,潘小荣来信说:“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新兵连的生活结束了,大家都等候者分到老连队,要和老兵们在一起了。有些人分到了汽车排,有些人分到了坦克排,还有少数人到了部队首长身边,或者当通讯员,或者当警卫员,或者当医务人员,而我则到了汽车排,当了一个汽车兵。”
这其实是潘万里一家最盼望的结果。
连着两封信,何牡丹考虑也应该给儿子回一封信了,也好让他知道家里的情况。可是,潘美丽虽然能看懂来信,但是,让她信,她现在是没有那个水平,毕竟她只是读过三年夜校啊。有些和她一样经历的人连读信都有问题啊。何牡丹想到了他二叔的女儿。他二叔是何牡丹对于小叔子潘万强的称呼,因为对于潘万强,何牡丹也不知道喊什么好。喊她小叔子,毕竟对方已经是小学的校长,喊他叔叔,似乎又委屈了自己,所以,她对于潘万强唯一的称呼就是他二叔。潘万强的女儿潘美晨刚好在家,听说大妈需要她帮忙给部队的潘小荣回信,潘美晨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潘万里的下一代中,他的大弟潘万邦和二弟潘万强的孩子中,只有潘美晨的年纪最接近潘小荣,其他的孩子和潘小荣相差太大了,所以,那个甩着羊角辫跳舞的潘美晨便成了和堂哥潘小荣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潘美晨虽然只比潘小荣的妹妹潘美丽大三岁,可是,对于潘美丽,她总是有些看不起,潘美丽也有些看不起潘美晨。因为潘美丽很少搭理潘美晨,所以,潘美晨认为这个人小鬼大的潘美丽是仗着她自己的长相才这么傲气的。其实,要论长相,潘美晨其实也并不差,匀称而颀长的身材,曲线分明的线条,鸭蛋似的脸蛋,只是皮肤没有潘美丽那么白而已。可是,潘美晨常常想:你长得白有什么用啊?我已经读到了初中,你连小学都还没有读,再过几年,你就更不如我了。
所以,当何牡丹请潘美晨替她写信的时候,潘美晨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她拿起写好了的信在潘美丽的眼前一晃,故意像是要气气潘美丽似的。然后对她的大妈何牡丹说:“大妈,信写好了,不认识字的人可不要给她看啊。”说着话,她故意用白眼珠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