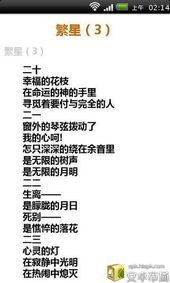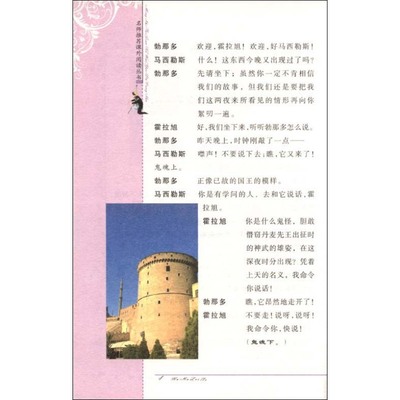大雁从天空飞过的时候,夕阳把树梢涂抹成金色。一群在场院上玩耍的孩子,突然间仰起脏兮兮的小脸,指着秋天寥廓的蓝天齐声喊叫:雁,雁,排成队,一只一只天上飞;雁,雁,一行行,头上飞过去南方……
父亲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牛粪,从地坑院陡峭的洞坡爬上来,扁担在他的肩头一颤一颤,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新鲜的牛粪弥漫着丝丝缕缕的白汽,挟带着牛尿的骚味儿热气腾腾地飘荡着。父亲爬上高高的粪堆,放下担子,抬脚一蹬,竹筐沿着粪堆骨骨碌碌滚下来,牛粪均匀地洒在粪堆上。父亲直起身子,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扭转头,顺着孩子们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了天空中愈来愈小的雁阵。他喘了一口气,笑了。夕阳给他的笑容渡上一层温暖的金色。父亲笑呵呵地说:哦,雁走了,过得真快!
顺着父亲笑容的方向,我看见天空的“人”字越来越小,越来越虚,最后消失在南岭上空的云团上。回过头,父亲不见了,却看见村路上走过一队瞎子,身上背着胡琴、梆子和长长短短的东西。瞎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一个拉着另一个衣服的后摆,寂然地从村路上走过。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并排,男的一手握着一根竹杖,一边探路一边走,另一只手却紧紧牵着身边女瞎子的手,给她引路。女瞎子后面,就是拉着衣服排成一队,背着“长枪短炮”的瞎子们。他们走得聚精会神,却又如履薄冰。夕阳照着他们淡然沧桑的面容,在大地上投下一排长长地、恍惚移动的影子,恍若在大地上游移的雁阵。
“噢,说书喽!说书喽!”
刚才还仰着脸看大雁的孩子们,蹦着喊着,各自跑向自己家里报信去了。
童年的岁月中,大雁,就是以这样一种温暖的画面,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上小学的时候,每当我拿着一张张奖状向父亲报喜,父亲都会用那双粗糙坚硬的大手,工工整整地把奖状贴在窑洞熏黑的墙壁上。退几步,左右端详,然后再走过去把奖状调整到他满意为止。那时候家里穷,父亲贴奖状不用糨糊。他从院子四周的酸枣树上,摘下几根尖利的枣刺当图钉,一根一根地把奖状扎在土墙上。他粗糙的大手抚过奖状时,发出哗哗啦啦的脆响。扎完了,依旧用那双粗糙坚硬的大手拍拍我的脑袋说:“好好学,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哩!”
我考上乡里的重点初中了,要到街上去住校读书。第一次离家,心里又高兴又害怕。我们村是全乡最小最落后的一个村,常常被街上人瞧不起,我心里面有着深深的自卑,在学校里很腼腆。班里有一个大村来的男孩,英俊活泼,但是成绩却不怎么好。母亲到表姐家走亲戚回来,对我说:“你在学校学习还不错的嘛!”
我说:“你咋知道的?”
母亲说:“那个常到村里来说书的瞎子,他儿子跟你同班,他们家跟你表姐是邻居,他对我说的。”
我说:“哪个瞎子呀?”
母亲说:“哪个瞎子呢,就是那个老牵着他媳妇手的瞎子呀!两口子都瞎,又生了一大窝娃娃,屋里面乱得进不去个人……”
随着母亲的絮叨,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夕阳下那一队雁阵一样的瞎子,静静地从村道上走过。同班那个英俊男孩的身影恍惚在这队列里走着,一直走到队伍前面那个女瞎子的后面,拉着她的衣背……我明白了,原来这个活泼的男孩,竟有着这样不幸的家庭。
又过了几年,我从一个腼腆敏感的少年,变成一个踏入青春门槛的小青年。一个夏雨蒙蒙的傍晚,我到表姐家里去,碰见一个在表姐家玩耍的少女,她显然只有十六、七岁,却美得让我心慌意乱,目光支离破碎,无所适从,脑海里立刻跳出八个老掉牙的字:“沉鱼落雁,羞花闭月。”表姐说,这就是她的邻居 ―― 瞎子的大女儿。我立刻就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学,他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我问表姐,他们家几个孩子?表姐说四个,老大是个男孩,其它三个都是女孩。我又偷偷地看那个美丽的小女孩,她就像一团火,让我激动,又让我羞怯。我得承认,迄今为止,美丽的女孩子我见过很多,但再也没有见过那么质朴而美丽的女孩子。
从表姐家回来的路上,我苦苦思索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命运有着这样奇怪的安排。又穷又瞎的瞎子夫妇,却生养下这样绝美的孩子。男孩高大英俊,女娃美妙绝伦。又过了几个月,大雁南飞的时候,我听说那个绝伦的美人儿,被街上铁匠的儿子糟蹋怀孕了。听人说,铁匠的儿子勾引了她,怀孕之后又抛弃了她。那年月未婚先孕是见不得人的丑事,铁匠有钱又有势,死不承认。可怜那个十六、七岁的美人儿,就只有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实在包不住了,在村邻撮合下,她被县城一个又老又丑的瘸子娶走了。
1991年秋天,我在武汉的一个大学里读书。星期天,一个人到东湖边的磨山去玩,在山顶上听见大雁嗷嗷的鸣叫声,引颈仰望,天空上一个气势宏伟的“入”字在快速移动,我马上就想起了父亲、故乡、童年的雁阵。嘴里喃喃出来的,却是小时候学过的课文 ――"秋天来了,大雁在天上飞过,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我坐在山巅一处树丛中,默默地思念着家乡,思念着父亲母亲。思绪游弋飘荡,我想大雁原本就是和我们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诗经》起步,飞过唐诗宋词,小说散文;飞过金元明清,草原湖泊;飞过金碧辉煌的宫墙和栉比鳞次的村庄;飞过离愁别恨和望眼欲穿,在无穷无尽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天空中飞啊,飞……而今,离开故乡的我们,经历过人世冷暖生离死别,再也不会像童年那样,跳着,喊着,“雁,雁,排成队,一只一只天上飞;雁,雁,一行行,头上飞过去南方……”。
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了黄土高原上。家里面的经济状况越发不堪。记不清因为啥,母亲决定我们家里说一场大书。每天晚上,晚饭过后,乡亲们都带着马扎小板,集中到我家院子里听书。每当梆子敲响,鼓乐响起,院子里鸦雀无声,连院子外面的场院上,秸秆上,也坐满了听书的乡亲。书场静悄悄的,只有明明灭灭的烟头和偶尔的咳嗽声,瞎子沧桑沙哑的声音带着听众,在寒冷的夜风中进入时间的隧道,在遥远的历史深处为一个个大忠大奸或者公子小姐的命运焦虑或愤怒,欢笑或咒骂。夜深的时候,书场里响起整齐的跺脚声,听书的乡亲终于抵挡不住料峭的寒风,又舍不得扔下牵魂挂心的故事,只有跺脚取暖。跺脚声越来越大,瞎子终于告一段落,开始说如同电视主持人一样的例行结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乡亲们陆续走后,我帮瞎子收拾说书的家什。口干舌燥的瞎子冻得瑟瑟发抖,双手冰凉如铁。我握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安排给他住的窑洞里面。拉亮灯,母亲给他端过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还有自家腌制的韭菜、辣椒。我坐在屋里,看父亲盛好面条递到他手里,瞎子三口两口就扒拉完了。如是者三,一盆面条已经底儿朝天了。
瞎子吃过面条,脸上露出活泛的笑容,空洞、真诚。空洞是由于缺少了眼神,真诚是因为他感到满足。由于和表姐家是邻居,瞎子和父母亲也算是熟人了。他睁着无神的眼睛笑吟吟地和父母亲聊着天,一边慢慢地喝着父亲给他端来的热茶。从他的话中我知道,他们那个曾经像雁阵一样的说书集体早已散伙了,承包责任制之后,群艺馆不管他们了,他只好自谋生路。不幸的是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死了,而他的那个和我曾经同窗的英俊儿子很早就离家出走了,好几年杳无音信。三个女儿都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人娶走了。小女儿被人带走的时候,才刚刚11岁,是被人当成干女儿带走的,养大了再给人家的儿子做媳妇。
他叹息着说:“没办法呀,这都是命!”
瞎子在我家说了三天大书,每天晚上都是我帮他收拾家什,握着他冰凉的手送他回屋。然后,看父亲给他盛夜宵面条,看他狼吞虎咽之后满足的面容。临走的时候,父亲塞给他十五块钱,算是对他说书的报酬。他坚辞不要,说每天五块钱是不管饭的,他在我家每天三顿饭加一顿夜宵,还收啥钱呢?父亲坚决地把钱塞给她,拉着他的手把他交给来接他的下家手里。
那好像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在乡村里现场听书了。很多年后,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在夜里,在寒冷的冬天的夜里,读海子的诗歌:“平原上有三个瞎子/要出远门;红色的手鼓在半夜/突然敲响;敲响,敲响/心在最远的地方沉睡……”我突然间想起瞎子冰凉的手就在我的手中,瘦骨嶙峋,瑟瑟发抖。夜,是那样的深那样的黑,那样的冷寂。我看见父亲在颤抖的灯光下给瞎子端过一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似乎听见瞎子吃面条的哧溜声。我的心百感交集,点上一根烟,痴痴地想……
后来,在山西,一个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左权县,朋友陪我去听一群走村串寨的瞎眼艺人,用苍凉的嗓音唱开花调,那曲词一下子就掏出了我埋藏在心底的泪――
谁说是桃花红呀,谁说是杏花白?
瞎瞎我活了这辈辈,我可没看出来!
山路路你就开花呀,漫天天你就长,
太阳开花什麽样,这辈子费思量。
胡琴琴你就开花呀,咯吱咯吱响,
父母养育我费心肠呀,兄弟情难忘。
梁柱柱你就开花呀,撑起了一间间房,
下辈子好歹睁开眼呀,来把这情报偿!
太行山你就开花呀,走也走不到头,
下辈子好歹睁开样呀,看看这圪梁和沟。
……
1997年12月,父亲走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在村里暂住一段时间陪母亲,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父亲给瞎子盛饭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我问表姐,那个说书的瞎子怎么样了?表姐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早死了!”
五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迟迟疑疑地说:“我给你说件事情,你别难过。”
我说:“什麽事情?”
母亲说:“你表姐死了……”
不让我难过,我从母亲的话里听出了悲伤!
我问:“怎么死的?”
母亲一声叹息,说:“跌死的,天不亮就起来到山上捋药,掉进别人的院子里跌死的,她才四十几岁啊!”
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2010年2月7日,我从深圳、珠海、澳门回来的第四天,窗外冷雨霏霏,年关的气氛被冷雨冲击得惨淡凄清。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仅仅二十天,我们村又走了两位老人,其中一位是我大伯。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无法排遣,打开电视,是2009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决赛的回放,当那个蒙族女歌手萨日娜用蒙语演唱那首熟悉的《鸿雁》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夕阳下父亲看着高飞的雁阵,流露出来的温暖的笑容;想起他粗糙的大手认认真真地往土墙上扎奖状时的情景;耳边仿佛响起粗糙的手抚过奖状哗啦哗啦的声音;想起父亲充满怜爱的教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的眼泪汩汩流淌。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父亲却什么也没有留下,除去慈爱,除去辛勤劳作的记忆,除去我们的悲伤。父亲走得决绝而坚定。如同童年的那个黄昏,我顺着他笑容的方向看雁阵在南天上消逝,回转头却看不见他一样。我看不见他,他的笑容却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听不见他的声音,满脑子都是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教诲。那个蒙古的歌手唱完了蒙语又开始唱汉语版的《鸿雁》,歌声忧伤而悠扬:鸿雁,蓝天上,阵阵排成行,天苍茫,雁何往,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秋草黄,江水长,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
凄冷的冬天深处,鸿雁在何方?曾经的亲人在何方?记忆中明亮温暖的童年在何方?我抬头看窗外,天空阴郁而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父亲、大伯、表姐、瞎子、我记忆中所有的亲人们,你们在哪里?我想你们,刻骨铭心!在这年关将至的时刻,在异乡,在关于大雁的忧伤的曲调中,我只能独自沉醉……
2011年02月10草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