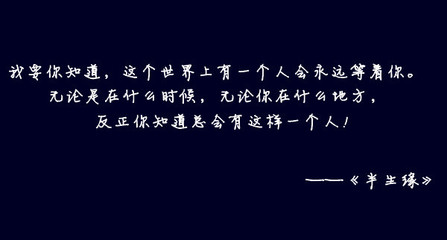关于莫言,由于我不认识他,只能莫言。
莫言这个人,很早以前,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的穷乡僻壤。是险些“该去见阎王”的黑孩,儿时经常能咯嘣咯嘣吃出煤渣子有甜味的他,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随时都有可能被他的大脑袋给压折。还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透明的红萝卜》里,“放个屁都怕把他震倒”的管漠业(莫言原名),却被一个屁给嘣到了瑞典的文学院。这里酸甜苦辣的细节谁知道?只有莫言。
我听说的莫言,是在国庆节的当天,车上的戏匣嘞里说:“除了日本的村上春树(莫言的对手),莫言最有可能于11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对于我是太过忽然,就像在慢长的夏夜,被一根烧熟了的大钢钻给打破了头。脑子混混的,令我莫言,一时竟想不起;1927年鲁迅拒绝去领诺贝尔奖(只是拒绝别人的想为他推荐提名)和85年后莫言获奖那个更重要?当时把我激动的;心脏都跳过了嗓子眼,可惜身边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危险,只得莫言。
国家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人,当天就致信,祝贺莫言。
我看到的莫言,却是空空的,什么内容也没有,是一片的空白,那是在他获奖后的省城书店,是他获奖两日后我的亲身经历。听着一阵阵都像是文人的询问:“有莫言吗?”“有莫言?”像是早就放好了几盘循环播放的录音带,标准的文人京腔解说词:“没有莫言”。“没有莫言。”
书店和我不一样,全在那懊悔着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都怪莫言。(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股市却有人利用了机会,7。72亿的资金,当天就疯狂的涌入了“莫言概念”板块。A股的红色救命稻草,就是莫言。
文学爱好者是真正的爱好者,据说莫言旧居门前一亩二分地里的胡萝卜缨子,只几天功夫,都被一群一群像是参加红色旅游的人像薅资本主义的羊毛一样,一人一根拿回家做了纪念,给一片一片地里的胡萝卜,撸得只剩下了成片成片光秃秃的头,在耀眼的光环下玲珑剔透、晶莹透明。那没有缨子的萝卜头,真像莫言。
可能是我寄居的城市太小,从他获奖后,我从来也没听到过有关作家,学者对这方面评价、赞誉的报导。我想,就是如果有也会如一群女人一般。当看到一对真正丰姿绰约的妙龄女郎的芳胸时,要么会说她是束(塑)的,要么会说她是文的,要么说太大,要么说太小,自己形不好的会说她是假的,反正多数的女人会说完不如她自己的充实以后,再去偷窥什么是,真的莫言。
我想不管他的作品是塑的还是文的,能获此殊荣,莫言的作品就应该激起国人对文学的热情,让文学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唯有这个事,不能莫言。
关于“莫言热”他自己说:“最多一个月就过去了。”关于他塑造的奖杯和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对“莫言热”的预期,我只能说,别都莫言。
我知道的莫言不多,只知道他得了这么大的奖他还谦虚的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对于他能代表世界当今的最高文学成就,我觉得他是听了(是他相像的)福克纳老头对他说的话,定下了比自己能力更高的目标,超越了自己。他不去为发财和成功操心,才是莫言。
以他的野心,他早就想建立一个文学共和国,一个饿怕了的孩子,辍过学的孩子,能倒背《新华字典》的孩子。一心想靠着写他“高密东北乡”旗帜的能力,当上共和国开国皇帝的人,当然莫言。
他净写些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草鱼虫、痴男浪女、地痞流氓,还写刁民泼妇,还想主宰这些东西和不是东西的东西。他只想着用笔,用语言,再加上他的点智慧,外加上点运气,就建国当皇帝的他,能不莫言。
你看他写的静,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能让一个小黑孩,听到了头发落地的声音。他能用笔打破常规,把旧世界的现存体系打的落花流水。能让带着勃勃生机的红太阳照亮了他的共和国,唯有莫言。
他也有像在《说说福克纳老头》里说福克纳的一些小毛病,比如他的偷懒,好忘,想省事等等的小毛病。他懒的时候也真是懒。在《一匹误入民宅的狼》里,他写国家不好的事,懒得只用了几笔:“到了近代,国家忘了控制人口,使这里人满为患…”那是忘了么?是他故意懒得写,他想省就省,真是大师。在没读过他的《狼》之前,我写《贵与贱》里的美元连体钞,也是写的忘了:“忘了剪裁,省了几道工序,也不用流通…”就不会偷懒,比他少忘了好多字。想起来,让我莫言。
你看他写吃窝头,像是他比列宁蹲监狱的年头还长似的:“一个窝窝头的眼里塞着腌黄瓜,一个窝窝头眼里栽着一根大葱。”我要是跟季羡林坐过牢也不会写得这么真实,还是莫言。
莫言的文学艺术能把混乱转换成为一种新的秩序,他能把他感觉到的和领悟到的东西再加以重新安排。在《怀抱鲜花的女人》他不写国家干部的好坏,却让一个心中充满邪念的海军上尉,在被女人身上喷吐的腐草的香气给艳遇后,让一只黑狗伴着女人、鲜花以及可以听到的味道和嗅到的声音,牢不可破的包围着伦理,笼罩着世态,吞噬着邪恶,影射着贱人的灵魂深处。能把他深恶痛绝的劣行写的那么平淡而又深邃,能写出悔罪的人把自己当成罪人,忏悔的人要对狗赎罪。还得莫言。
他能从低着头看到的鞋底和鞋跟不用看到大腿的上部,就知道路过的是什么人,他看着红裙子中轻轻踮起的白跟花袜高跟凉鞋就知道是个基层供销社胸脯干瘪的售货员。看到一群人迈步的速度,就能写出人们脸上的基本表情和人的思想岁月。唯有莫言
他能让一匹大黑狗在上尉还没被女人口腔中的草料香气弄得昏头涨脑时,在女人的裙下哀鸣。能让一只狗来表述作家的爱憎,非得莫言。

你再看他的生活体验,写的是多么的细致入微,而又不拘泥于客观写实,让真实在他奇诡的想象空间里展现。他写小石匠摸菊花,比他摸自己的胸还有感受“那只大手又轻轻地捂在姑娘硬邦邦的像窝窝头一样的乳房上。”他刻画的生活真实的比现实还真实。我经常经常饿得眼珠子发蓝,吃窝窝头时也没有这种感觉,也没见过他写的那样,“心在乳房下像鸽子一样乱扑腾。”莫言的文字很干净,他从来没把手往胸下面挪过半寸,他写的动作也很干净。干净到他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不愿意看到的真实。这一点一定会让一些作家,更加莫言。
看着莫言的照片,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比我没大多少的山东老头一样和蔼可亲。为了将莫言的“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诺贝尔奖颁奖词)。”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学到我的思想里,我真想和莫言的文学共和国建立一个私人的外交关系,只是在没有和他会见之前,我只能先做到,要很认真的,学习莫言。
2012年11月11日
于松原和易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