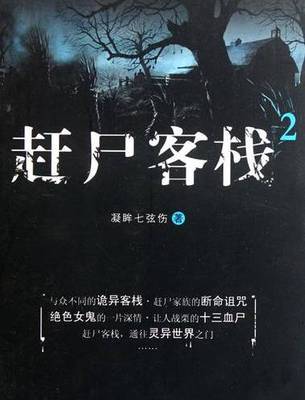《第九个寡妇》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她的转型作,作品讲述了中原地区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在土改时期藏匿其地主公爹的传奇故事,时间跨越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该书出版于2008年,并在2010年进行了改版再次印刷,本词条对本作品两个版本的基本信息分别进行了介绍,并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简介,这本书得到了编辑的大力推荐。除此之外,词条还对作者严歌苓的主要作品情况进行了补充介绍,并附有本书的精彩文摘。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
小说第九个寡妇_《第九个寡妇》[小说] -作品简介
一个背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发生了纷乱复杂的变化的历史阶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碎,进而发生了乌托邦的大混乱。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而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
小说第九个寡妇_《第九个寡妇》[小说] -作者简介
严歌苓严歌苓,女,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9年赴美留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 “百万长篇小说奖 ” 以及上海文学奖)、《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等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最近她以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赴宴者》将于2006年4月在美国、英国出版。
小说第九个寡妇_《第九个寡妇》[小说] -作品赏析
严歌苓她们都是在4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开始守寡的。从此史屯就有了九个花样年华的寡妇;最年长的也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四,叫王葡萄。后来寡妇们有了称号,叫作“英雄寡妇”,只有葡萄除外。年年收麦收谷,村里人都凑出五斗十斗送给英雄寡妇们,却没有葡萄的份儿。再后来,政府作大媒给年轻寡妇们寻上了好人家,葡萄还是自己焐自己的被窝,睡自己的素净觉。那个夏天黄昏村里人都在集上看几个闺女跟魏老婆赛秋千。魏老婆儿七十岁,年年摆擂台。一双小脚是站不住了,靠两个膝盖跪在踏板上,疯起来能把秋千绳悠成个圆满圈圈。就在魏老婆荡得石榴裙倒挂下来,遮住上身和头脸,枪声响了起来。人还噎在一声吆喝中,魏老已经砸在他们脚边,成了一泡血肉,谁也顾不上看看老婆子可还有气,一条街眨眼就空了,只有魏老婆的粉绿石榴裙忽扇一下,再忽扇一下。假如那天葡萄在街上,魏老婆说不定会多赛几年秋千。葡萄在,葡萄常赖在秋千上,急得魏老婆在下面骂。葡萄听见响枪也不会头朝下栽下来,把人拍成一泡子血肉。对于葡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听人们说:“几十万国军让十万日本鬼子打光了,洛城沦陷了!”她便说:“哦,沦陷了。”她想的是“沉陷”这词儿象外地来的,大地方来的。
葡萄那天给她公公收账去了。她公公看中她的死心眼,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往人家窑院墙上一扒,下面窑院里的人推磨、生火、做饭,她就眼巴巴看着。有时从早到晚,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她还在那儿扒着。要问她:“你不饥吗?”她说:“老饥呀。”假如人家说:“下来喝碗汤吧。”她便回答:“俺爹说,吃人嘴短,账就收不回来了。”人说:“不就欠你爹二斤‘美俘’钱吗?”她说:“一家欠二斤,俺家连汤也喝不上了。”
葡萄的公公叫孙怀清,家里排行老二,是史屯一带的大户,种五十几亩地,开一个店铺,前面卖百货,后面做糕饼,酿酱油、醋。周围四十个村子常常来孙二大的店卖芝麻、核桃仁、大豆,买回灯油、生漆、人丹、十滴水。过节和婚丧,点心、酱油都是从孙家店里订。收庄稼前,没现钱孙二大一律赊账。账是打下夏庄稼收一回,秋庄稼下来再收一回。眼看秋庄稼要黄了,还有欠账不还的。孙怀清便叫儿子去收。孙怀清嫌儿子太肉蛋,常常跑几天收不回钱。再逼他,他就装头疼脑热。葡萄这天说:“我去。”晚上就把钱装了回来。村里传闲话的人多,说孙怀清上了岁数忘了规矩,哪有一个年少媳妇敢往村外跑的。孙二大只当没听见。
走上魏坡的小山梁子,葡萄听见。
小说第九个寡妇_《第九个寡妇》[小说] -作品评价
四○-八○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下,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
小说第九个寡妇_《第九个寡妇》[小说] -读者评论
从这本书让大家重新去审视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原本政治化如此浓重的社会再作者的笔下,让你觉得似乎有些可笑。我不知道老一辈的人会怎样去看待这本书,和这书里的故事,原本让人觉得那些先进,模范的事情,改革。在那个寡妇面前显得那样的苍白,甚至有些可笑。有种颠覆的感觉。读完这本书,也许大家会体会到,如果可以真实的活着那该是一件多么畅快淋漓的事情。 ―― anita读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想到了两部作品和一个故事。两部作品,一个是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另一个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影片《地下》。故事是美国侵占伊拉克时的一则新闻,说一个伊拉克人得罪了萨达姆,在夹壁里生活了多年,直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才从夹壁中走出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到这两部作品和这个新闻,是因为《第九个寡妇》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孙怀清则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地窖与夹壁不过是一个隐喻,它通过对另一空间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指出现实空间的非正义性,从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不同的编码系统中,地窖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上述新闻中,便可以读解出对萨达姆政权的仇恨与对美军的热爱,而在《地下》中,则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至1995年的曲折历史。《白毛女》和《第九个寡妇》也是如此。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两种“人”是并不相同的,《白毛女》里的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兼小业主孙怀清,在小说中,他重复了喜儿由鬼变人的命运,而王葡萄作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喜儿(被地主家收养、欺凌的童养媳),反过来拯救了他,这使小说在多重意义上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
陈思和先生在此书的“跋语”中,以“慈母/大王”、“民间/政治”的二分法来把握与分析这篇小说,并在《古船》、《白鹿原》的文学史脉络上给予了高度肯定。有意思的是,在一篇论述《白毛女》的文章中,孟悦也以民间与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她认为在《白毛女》最初的歌剧剧本中,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民间伦理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保障了民间伦理的逻辑,共产党才得到了民心,获得了力量。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九个寡妇》中民间伦理的合法性,也论证了孙怀清的“政治”的合法性,在这里他无疑代表的是一种地主的立场。如果仍在《古船》、《白鹿原》的脉络中来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也就是“地主”翻身的历史,他们从剥削、压迫者,一变而成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化身。地主在文学中翻身当家做主人,现实中农民则饱受压迫,其中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第九个寡妇》可以看作不同阶层在时代中命运翻转的寓言
说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了重述,对以往的历史观也做了颠覆,在其视野中,1950―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作者同情的对象,用过去的话说,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而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经典作品中,这些恰恰是被批判、争取的对象,这些作品用大量篇幅赞扬的是农村中的“新人”,在梁生宝、萧长春等人身上寄予了农村的希望。
有意思的是,不仅《第九个寡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翻转,近期出现的一些其他作品也是如此,阎连科的《受活》以受活庄要退出“人民公社”为结构,莫言的《生死疲劳》则以蓝脸一根筋地坚持单干为主要线索。这些作品描写的同样是1950―70年代的农村,但与《三里湾》等作品相比,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其一,是不以认同、赞扬的态度来描写农业“合作化”和这段历史,而是大体持否定、讽刺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反映了人们对“合作化”的认识。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承包”的实行,否定合作化、赞扬“土地承包”成为了一种潮流,也成了80年代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土地承包”并非是对“合作化”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合作化的继承与改造。土地承包与“单干”所坚持的土地私有化不同,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而土地的集体所有正是“合作化”的重要成果,它打破了小农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同时土地的定期调整,也为避免贫富分化、保持社会安定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承包”政策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如何去与全球化的市场交易的问题;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合作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目前在河南、山东、东北都有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重新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对“合作化”的简单否定,如果不是思想懒惰,就是并非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其二,这些小说大多并非现实主义的,而采取了更多样的艺术形式与技巧。比如《受活》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狂想”,《生死疲劳》被认为是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第九个寡妇》具有更多现实主义的因素,但小说以故事性见长,更接近通俗小说。如果我们以对历史、现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来衡量,那么这些作品,在总体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三里湾》、《创业史》与《艳阳天》。后面这三部作品,虽然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但透过这一限制,我们能看到当时农村中不同阶层的心态和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它们所塑造出的一些人物,如王金生与范登高,如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如萧长春与弯弯绕、滚刀肉等等,既有时代的精神内涵,也有对民间文化、农民心理的深入了解。而《受活》、《生死疲劳》等作品,大多是从一个既定的理念出发,又没有对农村具体、生动的描绘,主题和人物都是主观化的,无法呈现出农村丰富、复杂的情景。自然,相对于现实主义的单一,“狂想”与魔幻现实主义在艺术上也显得比较多样,但手法上的翻新并不能掩盖其艺术上的苍白。
严歌苓的小说,多以结构精巧,善于描摹女性心理著称,这在《白蛇》、《扶桑》、《少女小渔》、《天浴》、《吴川是个黄女孩》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她近年来描写大陆题材的作品,如《天浴》、《第九个寡妇》,想法却似乎一直停留在80年代,对变化中的中国并没有思想与艺术上的敏感,这与她对海外移民题材的细致把握有着显著不同,之所以如此,或许是由于作家久居海外,对祖国的变化并无切身感受吧。 ――水面清圆
![第九个寡妇小说 《第九个寡妇》[小说] 《第九个寡妇》[小说]-作品简介,《第九个](http://img.413yy.cn/images/b/06230503/2318030506231479236451.jpg)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