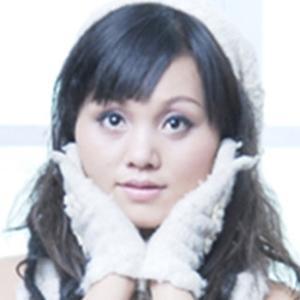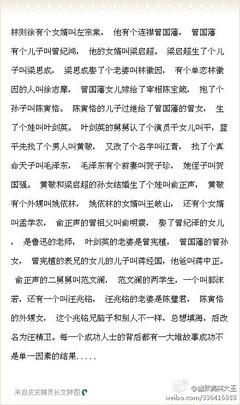那时,连小学生都被赶鸭子似的撵到田里割草、拾稻穗、摘棉花。我们被一种大潮裹挟着、涌动着,谁也不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知将有什么命运降临。
四月里,太阳爆得火,油菜花漾开了,田头场边村里村外像开了油坊似的,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香甜。我们割草,大人拌草。天将黑时,交秤,记工分。掌秤的横眉怒吼“你割几斤哪?见得着称吗?”我哇地哭了,这下可不得了啦,一个工分拿不到,还要被学校评为表现不好,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苍茫暮色已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圩埂上早稻田里已是虫舞蛙鸣蛇行,骨瘦如柴的我越急越割不动。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她正在粪堆塘里拌草,一对长辫子,乌亮亮,滑溜溜。她笑盈盈地说“等等,我割一把给她凑凑。”
“晓得你从塘里爬上来,要费多大功夫,误的工还不止一个工分呢。”
“就割一把。”说着,她就拄着粪叉从一人多深的粪堆塘里爬上来,只割一把,就把我的草篮子塞得鼓鼓的。
这样的芳姐死了,三十八岁,死于败血症,没钱治病。才三十八岁呀。(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我却常常想起她,因为她对于我的恩惠,还是别的什么?
就在开门办学、学生务农那档子,风行做无名英雄。一袋烟功夫翻一亩地的小芳怎肯落后?伙同几个姑娘夜里偷偷地掼粪堆塘,一夜掼三个。三个粪堆塘?要把三堆小山似的青草跟河泥、猪脚粪拌匀,或把塘里的绿肥翻到田垄上,45个工分就这么“无名”掉了,让粪叉破了腿还继续抢着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里下河地头的青草连天,而当杜鹃在柳梢头哀哀啼叫时,草便痴痴地往高里直窜,窜得腰高人深,空气里青草味混合着菜花香、泥土芳香、各种昆虫吃饱呃出的气味儿,像是屋子里泡了碗方便面,钻鼻子,沁心肺。
想起芳姐,就做梦,梦见金山寺大雄宝殿檐顶镂空的“度一切苦厄”五个字变成五个石磙子滚过来;我呢,两腿直蹬,拼命躲避退让,就是躲不过,直到被它轧扁了,终于压成一张土灰的纸。
听说县医院曾把她当作特殊病例,村里二麻子悻悻地说“到底是劳模,是党员。”可她十八入党,二十八退党,因为她不识字,尽管在扫盲班识了不少字。后来知道:败血症近二十年才发病,是特殊病例。医生推测,可能让什么锈钉刮破过。我疑心是粪叉刮破的。
芳姐死了,生命在她如压缩药丸一般苦。那年头,劳动苦,日子紧,没什么吃的,没什么穿的,也没什么好好玩的。一件衣服,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老三穿后还纳鞋底。一撮小咸菜,早上吃,中上吃,晚上吃,吃剩的卤汁还泡稀饭。一年到头,就指望看场样板戏,或听听苦滋滋的淮剧《蔡金莲》;可她呢,一边还纳鞋底,一个晚上纳一双鞋底。
文化大革命那阵子,乡下人起名字就爱起个芳啊英的,几乎村村都有小芳,不知有多少小芳姑娘呢。
好几年,面对遥遥暗夜,我总做那样的梦,梦一醒,身上汗涔涔的。
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么热情善良、这么能干又要强劳动起来不留余力的小芳姑娘,怎么会这样死呢?这是怎样的苦厄呢?
当你为你汲汲追求的所累所苦时,你的生命就会过早地被吞噬;
当心壶的水倾倒时,生命之水就会迅速离你消散而去。
多年来,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那些灼热的光环,尽管我工作起来如小芳那么疯狂。“为而不有”那毕竟是禅的安详,我辈很难很难修炼得道。
或许生命注定不能化做那朵莲花,功名利禄也不能全抛下;或许如佛所说我们今生注定要度一切苦厄,包括被某种强大的势力裹挟,压缩成药丸;可有谁情愿就这样把此生抛掷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