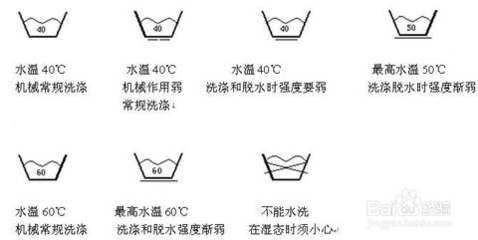拜山头是什么意思?
旧时匪盗猖獗,匪帮几乎都扎根于山上,与官府对抗。拜山头是入帮会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内容是内帮会成员的引见,因此成了入帮会的俗称。现在引申到入教,入职场等场合。
富商张新明曾电话新市委书记:也不来我这拜山头
张新明悠游于山西政商两界,长袖善舞,予取予求,显然与市场无关、与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正是因为官场的大面积崩塌,才导致市场的失序,以致“丛林原则”横行,正当企业与一般民众成为鱼肉。
从2014年8月至今,“山西首富”张新明销声已有数月,案情仍是一团迷雾。据《财经》杂志报道,张新明被带走后,山西官场地震不断。而审计署则在核查张新明如何获得了大宁金海煤田采矿权;有关部门也在调查2007年一起古交市黑矿事故,矿主疑似张新明兄弟。报道表示,“目前张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张新明的能量有多大?仅就目前媒体粗粗勾勒出来的“政商图谱”,或可得出一个大致判断,即,张新明在山西官场上的渗透有多深,则山西诸多官员就在张新明的生意上介入有多深。二者可能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共谋”。
据报道,2000年就任古交市委书记的毋青松,一到任就接到张的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尽管毋青松并未就范,但这并无损张新明在古交的“权威”,更不代表山西省其他官员也会主动拒绝张新明。
例证一,2003年,为了办理大宁金海煤矿基层审批手续,张新明带队到晋城,据目击者披露,“晋城市委市政府接到上级要求,阳城县和晋城市两级政府机构联合办公,一天内要为张新明办好所有审批手续。”
例证二,多年来,张新明家族在古交控制其他矿山的手法也如出一辙,耐人寻味:矿主“突然”犯事,公检法机关介入,张新明出面斡旋,条件是免费入股甚至控股煤矿,或是矿主随张到澳门一赌、输惨。
若媒体报道的情况属实,张新明悠游于山西政商两界,长袖善舞,予取予求,显然与市场无关、与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正是因为官场的大面积崩塌,才导致市场的失序,以致“丛林原则”横行,正当企业与一般民众成为鱼肉。也因此,有必要追问,究竟是谁成就了“张新明们”?
遗憾的是,尽管经由媒体的不懈追踪,初步呈现出张新明背后的权力拼图,但因为细节有待补充、擦亮,距离真正的还原还为时尚早。不过,从其东窗事发后,山西省国土、煤炭、公安系统一批高官落马的情形看,事件仍在发酵之中。接下来还会牵扯到哪些官员,这些官员陷入有多深,有待进一步观察,对此,必须“有一个查处一个”,严肃问责。
而除了问责具体的官员之外,更值得忧虑的,则是当地官商勾结的深厚土壤。可以说,张新明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个例,而是有着浓重的制度背景。其中的关键,在于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强力干预,且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样,只要搞定了权力,也就赢得了市场;搞定的官员级别越高,则可变现的利益就越大。也即,以利益俘获权力,以权力攫取利益,直至官商通吃,无往而不利。
密集的政商交集与互动,既为张新明高悬起“山西首富”、“山西赌王”、“太原第二组织部长”的名号,也给山西官场带来了塌方式腐败。“太原官场从此以讹传讹,说张新明中央有人,”上述人士笑称,“甚至开始有人找张新明跑官。”其“太原第二组织部长”的外号,因此出现。当然,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听任“张新明们”一手遮天,官商通吃,必然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堰塞整个社会的激情与创造力,如同山西一位律师所言,“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信心”。
在查处张新明及其背后隐秘权力的同时,也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制度性土壤,廓清迷雾,除恶务尽,方可真正给民众以信心。

《财经》记者跟踪报道这个著名的“问题富豪”一年多,越到后来,越感觉此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目前张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0年调任古交市委书记的毋青松,甫一到任,就接到张新明的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毋青松大怒,在古交“三干会”上公开讲出了此事,“我就一个女儿,我怕什么?你张新明有什么,我可一清二楚,我倒要看看谁拜谁!”
古交现任市长贾慕权,2013年刚上任就搞大接访,接访的第一人是古交马兰滩开木材销售公司的邢亮平。邢亮平称,古交市康福才等三名干部殴打自己,勾结张新明霸占了木材厂场地,盖了50间房子出租获利。
贾慕权立即调来古交国土、水利、城管等部门现场办公,几家单位确认,邢亮平的企业占地手续完善,而康福才等人的出租房是违章建筑,影响河道行洪。贾慕权对着古交电视台镜头拍板,要求限期拆除违章建筑,公安介入打人事件,纪委约谈三位干部,引来围观群众叫好。
但是,这位市长说话根本不灵。随着张新明介入,违章建筑至今未拆,公安也不愿为邢亮平做伤情鉴定,反称邢亮平也把对方打伤,“再告状连你一块抓”。
当地的一个说法是:在古交有麻烦,找“二汉”张新明,比找市长管用。
“中纪委宣布山西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位山西省著名律师评论说,“张新明验证了这一结论。他更大的危害,是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