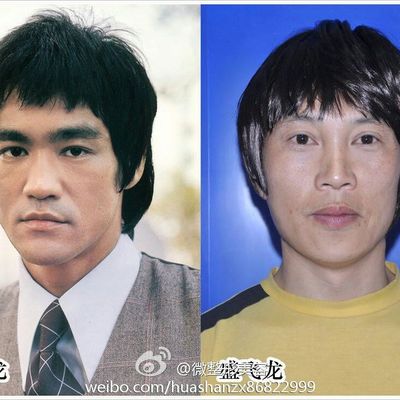《家庭幸福》由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出版.
家庭幸福_《家庭幸福》 -内容
《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1858~1859),有托尔斯泰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
家庭幸福_《家庭幸福》 -创作
一八五九年前后,托尔斯泰的两个兄弟德米特里和尼古拉都先后因肺病而去世。托尔斯泰自己也得了严重的肺病。那时期他还跟屠格涅夫发生了造成终生不和的剧烈争吵,甚至到了要动枪决斗的地步。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过渡时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托尔斯泰都处于极其不佳的状态。他彷徨,他迷茫,他矛盾......但突然奇迹发生了。托尔斯泰爱上了一个清纯的少女,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真是这一爱情的奇迹使托尔斯泰写出了至那时为止最”精纯”的作品――《家庭幸福》。三年后他与索菲娅结了婚。这部小说写的是爱情和婚姻的事情,据说是托尔斯泰自己与索菲娅结婚前后的事实。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出在前(1859年),结婚在后(1862年)。难道是托尔斯泰在结婚前就设想他的爱情和婚姻应该是如此的吗?济之先生说,读了这本书可以从中得到”爱情与结婚的真缔。”罗曼?罗兰也说,”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家庭幸福》具有一部拉辛式作品的完美。””欲洞悉作者的文学,不能不读此书。”(注:拉辛,JeanRacine,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诗人。拉辛式作品以其情节紧凑,语言艺术性高而著称。
家庭幸福_《家庭幸福》 -翻译
济之先生于1919年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翻译《家庭幸福》,年方二十岁。非常有趣的是,那年十月的一天,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俞颂华先生收到了耿济之和瞿秋白从北京寄来的两篇译文《告妇女》和《答论驳《告妇女》之节录》。这两篇都是托尔斯泰的短文。颂华先生立即被这两篇文章的立意吸引住了,他同时也被耿,瞿两位的翻译文笔和文学才华深深吸引了,决定马上刊登。没想到这两篇短文把颂华和济之从此联系在一起,开始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友谊,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很快地又成了连襟。1919年底,济之先生的父母向太仓一家钱姓大户的小女福芝为济之托媒。没想到俞颂华正是钱家大女儿梅先的夫婿。世上竟有如此之巧事!梅先那时正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颂华和梅先的极力撮合下,1920年8月,济之在颂华陪同下,福芝在钱老太太的陪同下在北京南城游艺院的一座小木桥上相会了。他们从桥的两头走到中间,互相只悄悄地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却一见钟情。这天正是福芝的生曰,农历七月初七。他们真是应了中国古时候的一个美丽的神话,一南一北,”鹊桥相会”啊!济之与秋白译的那两篇托尔斯泰的短文就是搭桥的喜鹊。不久,济之和福芝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订了亲。那天,他们吃的是北京来今雨轩最有名的冬菜包子......
这真是一段令后人赞叹不巳的佳话。托尔斯泰是在写作《家庭幸福》时完成了他的爱情与婚姻,而济之先生是在翻译《家庭幸福》时也完成了他的爱情和婚姻。托尔斯泰的婚姻并不很完美,但是,济之先生的婚姻却是非常令人欣慕的。也许这正是托尔斯泰《家庭幸福》的祝福吧!
家庭幸福_《家庭幸福》 -妙语
社交本身的害处倒不大,可社交界的填不满的欲望――却是不好的和丑恶的。
――《家庭幸福》
我要的不是我已经到手的东西,而是一种斗争的生活;我要让感情做生活的向导,而不是让生活去指导感情。
――《家庭幸福》
一个人不会忍受孤独是不好的。
――《家庭幸福》
在钟爱的人的面前,显示心灵的优点,比显示外形的美更好,更有价值。
――《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_《家庭幸福》 -摘录
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两个月的乡村幽居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但这两个月所体验的感情、激动和幸福足足抵得上一生。我们俩关于村居生活的梦想实现得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过,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比我们的梦想差。没有我出嫁前所想象的那种认真的劳动,没有为了承担义务而自我牺牲,也没有为别人而生活;有的只是彼此相爱的自私的感情、被爱的欲望,老是无缘无故地感到快乐,并且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不错,他有时到书房工作,有时进城办事,或者为农活奔忙,但我看出,他离开我是多么痛苦。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只要我不在,世上一切对他都是没有意思的,他不明白怎么能去干那种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看竖,弹琴,陪伴婆婆,到学校教书,而我做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同他有关,并能博得他的称赞;但只要想到什么同他无关的事,我的手就垂下来,而且一想到世界上除了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可笑。也许这是一种不好的自私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使我感到幸福,并且使我高出于全世界之上。对我来说,世界上只存在他一个人,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任何其他事物活着,我只能为他活着,并且做一个他所希望的那样的人。他则认为我是世界上具有一切美德的十全十美的女人;我也就竭力要在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面前作一个这样的女人。
“是的,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在春天,”他仿佛在回忆往事,说,“我也曾满怀希望在夜里坐着,一直坐到天亮,那是些多么美好的夜晚哪!……不过当时一切都还在前面,可现在一切都已过去,现在我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我觉得很快活。”
“难道你什么也不想要了?”我问。
“我不想要任何办不到的事,”他猜透我的心思,回答。“啊,你把头发都淋湿了,”他添加说,像爱抚孩子那样有用手抚摸我的头发,“你羡慕树叶、青草,因为它们受到雨水的滋润,因此你想变成树叶、变成青草、变成雨。可我只欣赏它们,就像欣赏世间一切美好、年轻和幸福的事物那样。
“难道你对过去的一切就一点也不留恋吗?”我继续问他,觉得心情越来越沉重。
他沉思起来,又默不作声。我看出他要坦率地回答我。
“不留恋!”他简短地回答。
“不是实话!不是实话!”我转过身对着他,瞧着他的眼睛说:“你不留恋过去吗?”
“不留恋!”他重复说,“我感激过去,但并不留恋。”
“难道你不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吗?”我说。
他转过身去望着花园。
“不想,就像我不想长出翅膀来一样,”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不,我说我不留恋过去,那不是实话。不,我伤心,我为那已经没有和不可能再有的爱情而哭泣。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不知道。爱情还在,但已不是原来的爱情,只留下了爱情的位置,但这爱已饱经沧桑,不再有力量,也不再那么诱人,只剩下回忆和感激,不过……”
“别这么说了……”我打断他的话,“让一切都恢复原状吧……要知道这是可能的,是吗?”我瞧着他的眼睛问。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平静的,但没有看透我的眼睛。
我这样说时就已感到,我所希望和请求他的事是办不到的。他安详而温顺地微微一笑,我觉得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笑。
“你还那么年轻,可是我已经老了,”他说,“我身上已没有你所追求的东西;何必欺骗自己呢?”他添加说,依旧那么微笑着。
我默默地站在他身边,心里感到平静些了。
“我们不要竭力去恢复原来的生活,”他继续说,“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原来的焦虑和激动都没有了,那真该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追求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够幸福的了。现在我们应该隐退,给他们让路,”他说,指指抱着万尼亚走到凉台门口站住的奶妈。“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他结束说,弯下腰来吻吻我的额头。那不是爱人而是一个老朋友的亲吻。
 爱华网
爱华网